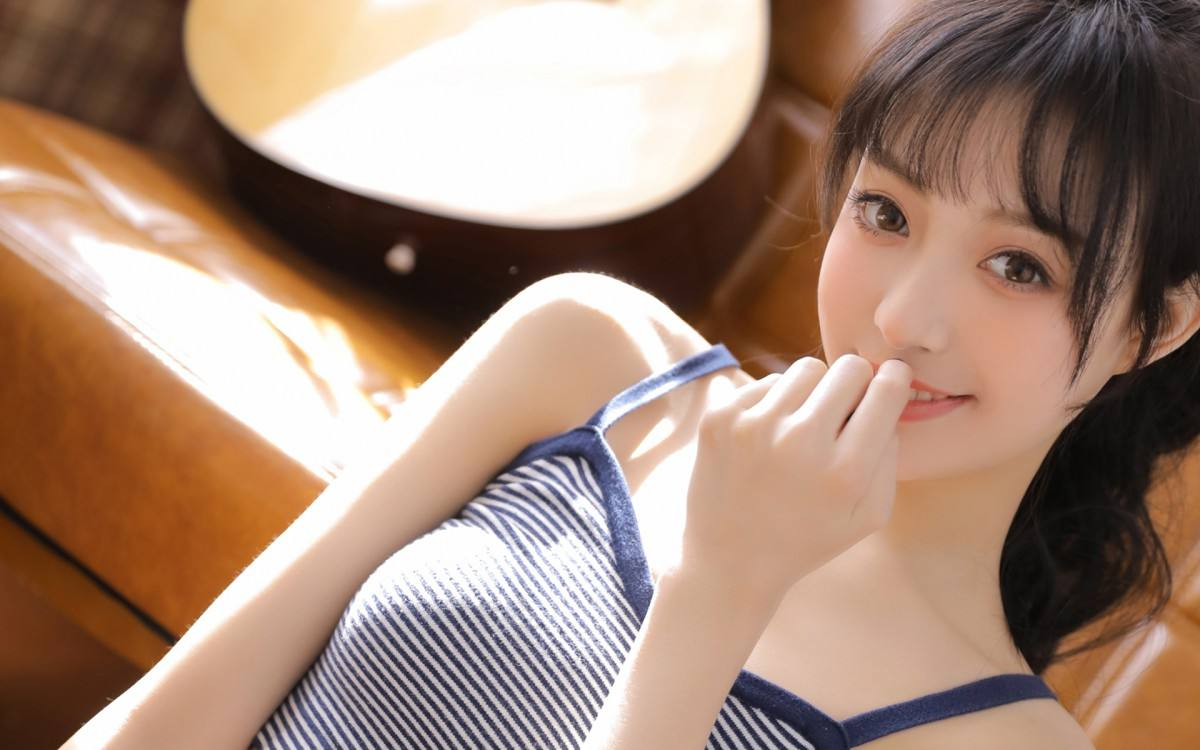性别与教育研究学者崔乐:恐同影响性少数学生学业及心理健康
高校教材应该如何定义同性恋?
9月14日,发布了《败诉“同性恋是病”教材案原告提交上诉状:放弃意味着认同》一文引发公众关注,有关“同性恋是否属于性心理障碍”的争辩此起彼伏。
注意到,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北京同志中心协作发布了《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文霭洁(Agi Veres)在该报告前言写道,在亚太地区(包含中国在内),性少数人群往往是社会中最为边缘、最为弱势的群体之一。历史告诉我们,除非我们对少数族群加以认真清点,否则他们就根本“不作数”。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我们一向以终结不平等和对少数人群的排斥为使命。切莫忘记,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的根本原则和使命,就是“不让一人落伍”。
文霭洁总结认为,在中国,性少数人群依然生活在阴影当中,只有 5% 的性少数人士公开了他们的性身份。绝大部分 LGBT(性少数群体)人士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受歧视,尤其是在家庭内部;来自家人的排拒和凌辱是最为根深蒂固、刻骨铭心的。不过,另一方面,该报告也展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进展。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性少数理应受到平等对待,充分享受各种社会服务。大多数受访者同样赞成制定和推行专门政策,尊重 LGBT 人群的地位,保护他们免受歧视。更为重要的是,这份报告描绘了一个正在转变中的国家。
可见,社会的包容度会对性少数人群的身份认知产生影响。性别与教育研究学者崔乐认为,恐同教材在教学过程中会对师生带来多重负面影响。对于异性恋学生来说,恐同教材可能会误导他们对同性恋的认知,进而导致偏见、歧视甚至霸凌;而对于性少数学生来说,教材本身的权威性可能会阻碍他们接纳自己的身份,增加心理健康风险。
崔乐曾在中国、俄罗斯、新西兰等国家的高校任教,同时他也是一位同性恋者。目前他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攻读博士,并担任学校助教。
以下是崔乐的自述:
七年前,当我还在广东一所大学任教时,有次我在性别议题的教学中提到了同性恋。下课后,一个女生站在教室门口怯怯地问我:“老师,你看到同性恋不害怕吗?”
她并不知道她面对的是一个同性恋教师,那时的我还不敢出柜。
我的学生对同性恋的恐惧并不值得意外,日常的校园生活中看不到任何真实的同性恋,大量教材以“性变态、精神疾病、心理障碍”来定义这一身份。
对同性恋心怀恐惧的不只是学生,用于师资培训的恐同教材还会塑造恐同的教师。在我2013年入职高校前,根据广东省教育厅规定参加了岗前培训。指定教材《高等教育心理学》(广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罗列的“大学生常见的心理疾病”中,“同性恋”被认定为“性变态”之一,“应该对他们进行心理治疗,帮助他们改变病态行为,而不是将他们简单地除名了事”。
还好有一些学生在推动改变。2016年,大学生秋白因恐同教材起诉教育部,以败诉告终。2017年,大学生西西因恐同教材起诉高校出版社,历时三年,于2020年一审败诉。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90年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剔除,西西案中的法院仍然认为教材中“同性恋是病”不属于“知识性差错”,大量教材中病理化、污名化同性恋的话语仍然存在。
恐同教材在教学过程中会对师生带来多重的负面影响。对于教师来说,照本宣科会强化同性恋污名,被认为发表歧视言论,可能遭到学生的反对;不按照教材的立场教学,或发表支持同性恋权利的言论,可能会被保守的高校领导层认为违反教学纪律。对于异性恋学生来说,恐同教材可能会误导他们对同性恋的认知,进而导致偏见、歧视甚至霸凌;对于性少数学生来说,教材本身的权威性可能会阻碍他们接纳自己的身份,增加心理健康风险。 2017年,华中科技大学的两名学生在校园举起“让同性恋远离大学校园”的标语。本文均为受访者供图恐同的校园环境会对性少数学生的学业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由公益机构“同语”2016年发布的一项针对2077名中国性与性别少数学生的调查显示,只有11.07%的学生在校园完全出柜,23%的学生报告在过去一年因性与性别少数身份而成绩下降。由北京师范大学学者2019年发表的一项针对732名LGBT学生的调查显示, LGBT学生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风险,约有85%的学生感到情绪低落,40%的学生有过自杀想法。
2017年,华中科技大学的两名学生在校园举起“让同性恋远离大学校园”的标语。本文均为受访者供图恐同的校园环境会对性少数学生的学业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由公益机构“同语”2016年发布的一项针对2077名中国性与性别少数学生的调查显示,只有11.07%的学生在校园完全出柜,23%的学生报告在过去一年因性与性别少数身份而成绩下降。由北京师范大学学者2019年发表的一项针对732名LGBT学生的调查显示, LGBT学生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风险,约有85%的学生感到情绪低落,40%的学生有过自杀想法。
另一群在校园里需要隐藏身份的是同性恋教师。我的博士研究访谈了40位中国高校的男同性恋教师,他们大多数需要以异性婚姻或虚构女友来伪装异性恋。一些教师认为他们需要比异性恋教师更加努力工作,以出色的研究产出应对身份暴露可能带来的风险。在进行同性恋议题的教学时,许多教师只是一带而过,或有意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以避免身份暴露、学生反对或违反教学纪律。一些从事同性恋研究的教师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有意保持低调,有的则出于对学术发表与申请资助的顾虑而放弃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指出,校园中的恐同事件不应只是被视为孤立的个案,而应检视导致恐同事件发生的环境,推动校园环境的改变,包括颁布反歧视的校园政策等。对于中国高校来说,这些建议也许并不现实——如果我们的教材还不能承认同性恋不是病。 性别与教育研究学者崔乐,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生。
性别与教育研究学者崔乐,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