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上是什么意思_霸上的前世今生
“霸上”是长安(今西安)东部一处军事要地,史书中对其地理位置有不同的记载,表明历代“霸上”地理位置有所不同。
(一)“三家注”分析
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文献对“霸上”地理位置有确切记载——即“应劭曰”、《水经注》和“《庙记》云”。
东汉桓帝时期学者应劭对当世“霸上”地理位置有明确描述,今存两种“应劭曰”:一是《汉书·高帝纪》:“沛公至霸上。应劭曰:霸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史记·集解》、《汉书注》、《资治通鉴》等与此相同;二是《水经注·渭水》:“应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长安东二十里,即霸城是也。”存有两种不同距离记载是因东汉、北魏“里制”长度不同,现以汉长安城宣平门(今未央区青门口村西)为基准点依“三十里(约为12000米)”向东测距,即在灞桥区新筑陆旗营一带(“霸城”遗址所在地),那么《水经注》与“应劭曰”所述“霸上”均指“霸城”。郦氏为证明“霸城”就是“霸上”还专门用刘邦逃归路线的距离进行分析对证,《水经注》载:“自新丰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则霸水,西二十里则长安城。应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长安东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旧停军处,东去新丰既远,何由项伯夜与张良共见高祖乎?”在驳斥郭缘生《述征记》后郦氏明言“霸城”就是“霸上”。今认定“霸上”在“灞桥东部”的学者皆依此段记载。但《水经注》又载:“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

《史记》秦襄王葬芷阳者是也。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认定“霸上”在白鹿原或“芷阳”者皆从此段记载。现从白鹿原地理位置和文献传抄皆可见此段记载确有讹误,“《三秦记》云:白鹿原东有霸川之西坂,故芷阳也。”又《水经注》载:“皇甫谧曰:秦庄王葬于芷阳之骊山,京兆东南霸陵山”,可知西晋学者皇甫谧已将白鹿原上的“汉文帝霸陵”和“芷阳坂”上的“秦芷阳陵区”混为一谈,皆放在灞河西岸的白鹿原上,郦氏《水经注》只是继续沿袭了皇甫谧的讹误。根据考古调查、发掘已证实秦芷阳城、(骊山)芷阳陵区、汉霸陵邑均在今灞河东岸铜人原(芷阳坂),仅有汉文帝霸陵位于灞河西岸白鹿原,是为“京兆东南霸陵山”或简称“霸陵”。按“秦襄王葬芷阳者是也,谓之霸上”、“秦芷阳宫在霸上”表明郦氏此段本意实为“芷阳陵区”“秦芷阳(城)”一带是为“霸上”。而同时期“《庙记》云:霸城,汉文帝筑。沛公入关,遂至霸上,即此也。”“(正义)《庙记》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两段记载的本意仍是指汉文帝“霸陵邑(城)”是“霸上”而非汉文帝陵墓(霸陵),这在颜师古“按”中已作说明。汉文帝“霸陵邑”承袭秦“芷阳乡”而来、同在灞河东岸“芷阳坂”上,可知“《庙记》云”所述“霸上”就是《水经注》所述“芷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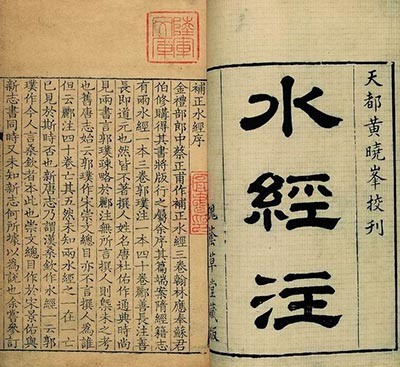
经分析可见,“三家注”中载有两个不同的“霸上”——“霸城”和“芷阳”,且从《水经注》中对“霸城”即“霸上”论证反映出当世学者已不知汉高祖驻军的秦汉“霸上”地理位置所在,故此郦氏才不加详辨地“广征博引”,但其自相矛盾记载却引起严重的混淆。
(二)史书所见“霸上”地理位置线索分析
除“三家注”外,正史中能提供“霸上”地理位置线索的主要有以下两条:
“霸上”与白鹿原、灞河之关系。《晋书·桓温传》:“温军力战,生众乃散。雄又与将军桓冲战白鹿原,又为冲所破。雄遂驰袭司马勋,勋退次女娲堡。温进至霸上……军粮不属,收三千余口而还。”表明白鹿原与“霸上”并非一地;《晋书·王猛载记》:“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魏书·司马聃》:“初,温次灞上,其部将振武将军、顺阳太守薛珍劝温径进逼城,温弗从,珍以偏师独济,颇有所获。”桓温“不渡霸水”、太守薛珍“独济”灞水表明桓温驻军的“霸上”在灞河以东。

“霸上”与武关道、潼关道、蒲关道之关系。“霸上”控制着武关道、潼关道(函谷道),史有明载。《晋书·桓温传》:“(桓温)别军攻上洛,获苻健荆州刺史郭敬,进击青泥,破之。”桓温自青泥关攻入关中后驻军“霸上”,说明“霸上”控制着武关道;《周书·文帝纪上》:“八月,齐神武袭陷潼关,侵华阴。太祖率诸军屯霸上以待之。齐神武留其将薛瑾守关而退。”说明“霸上”控制着潼关道(函谷道),故在此专谈“霸上”与蒲关道之关系。辛德勇先生曾据《弘明集》推定“蒲关道”与其它两路均汇于“霸上”,《弘明集》载:“近姚略叔父为晋王。于河东蒲阪古老所谓阿育王寺处。见有光明。凿求得佛遗骨。于石函银匣之中光曜殊常。随略迎都。于霸上比丘今见在新寺。由此观之。有佛事于齐晋之地久矣哉。”]但《弘明集》并未详载“舍利”入长安的确切路线,从蒲坂至长安亦可绕经潼关循潼关道(函谷道)至“霸上”入长安,仅凭此段记载难以确定“霸上”位于三路交汇,且其推定“三路交汇”于“霸上”的关键是在灞河入渭处以东存在“东渭桥”,但魏晋南北朝时并无“东渭桥”,原因有三:首先,在王家堡古桥发现以前,学者多据高陵耿镇唐东渭桥遗址和《高陵地方志》推测历代“东渭桥”均位于灞河东岸(高陵耿镇),但王家堡古桥的发现证明西汉东渭桥实在灞河西岸,否定了原有推论;其次,《三辅决录》、《三辅黄图》、《水经注》等文献对便门桥(西渭桥)、渭桥(中渭桥)、灞桥沿袭使用记载详实且均已被考古工作证实,却皆不载“东渭桥”,这绝非文献“失载”而是说明该时期并无“东渭桥”,且今在耿镇唐东渭桥遗址以南渭河故道上亦未发现同时期古桥梁遗迹;最后,从正史文献分析亦可推知“东渭桥”不应存在,否则无法合理解释一些历史事件,《资治通鉴·晋纪》载:“王镇恶请水军自河入渭以趋长安,裕许之。秦恢武将军姚难自香城引兵而西。香城在渭水之北,蒲津之口。恢武将军盖姚秦创置。镇恶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还屯石桥以为之援……难奔长安。”后秦“香城”失守后晋军循蒲关道进攻长安时,姚泓随即放弃“霸上”退守灞河以西的石桥(饮马桥)并布置渭北“泾上”防御线,若存在“东渭桥”使三路汇于“霸上”,姚泓便可在灞河以东“霸上”迎战晋军而不必退兵灞河以西;《周书·文帝纪下》载:“东魏遣其将司马子如寇潼关,太祖军霸上,子如乃回军自蒲津寇华州,刺史王罴击走之。”在获悉周太祖驻军“霸上”后司马子如从潼关改由蒲关道攻长安,希望能从渭河北岸避开周军主力以达到突袭长安的目的,如果存在“东渭桥”使三路汇于“霸上”,那么司马子如终将面对周军主力而无需绕行改道。经以上分析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蒲关道、潼关道(函谷道)与秦汉时期走向大致相同,即两路基本平行的循渭河北、南岸向西直入长安,此时蒲关道途经“渭桥”而潼关道(函谷道)途经“灞桥”。位于灞河以东的“霸上”仅是控制潼关道(函谷道)和武关道的军事要地。



经分析正史文献可知,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霸上”位于灞河以东且控制着潼关道(函谷道)和武关道。
(三)地区文化遗存分析
经文献分析后可见,“三家注”所载“芷阳”和“霸城”均能控制潼关道(函谷道)和武关道,孰是孰非还需结合地区文化遗存进行分析。
“芷阳”。1982年,张海云调查、试掘了临潼区韩峪乡油王村西、南两处地点,出土了菱形纹、方格纹砖、内麻点纹瓦、云纹瓦当、文字瓦当、“芷”字陶文器物残片、五铢、货布、铜铁箭镞、铁质农具等文物,该地当为“秦芷阳城”“汉霸陵(邑)城”遗址所在区域,调查所见两汉及新莽时期文物表明霸陵城至多沿用到新莽时期。此外,在“芷阳(霸陵邑)”附近亦有大量秦汉文化遗存,油王村东1.5公里处是“芷阳陵区(秦东陵)”、北1.5公里是窑村汉墓(汉初),根据历年来调查及农民取土过程中暴露的墓葬情况看,铜人原顶一带墓葬多为战国时期或稍晚,表明秦汉时期人们在此区域的生活、生产活动频繁。但此地却无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遗存,《水经注》亦称之为“霸城县故城”:“(漕渠)又东迳新丰县,右会故渠,渠上承霸水,东北迳霸城县故城南,汉文帝之霸陵县也,王莽更之曰水章。”明载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此城已废弃不用。

“霸城”。“《三秦记》云:霸城,秦穆公筑为宫,因名霸城。汉于此置霸陵。”但未得考古资料实证。现据正史文献及考古资料仅证“霸城县”始置于曹魏时期,“霸城”是其县治《水经注》载:“(霸水)东迳霸城北,又东迳子楚陵北。”又“《关中记》曰:昌陵在霸城东二十里。”该城在北魏时期仍然沿用,且与“霸城县故城(汉霸陵城)”并无承袭关系。今在灞桥区陆旗营至谢村一带发现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遗存,刘庆柱、李毓芳据此指出魏晋南北朝“霸城”遗址即在此地,且据两汉墓葬分部规律来看,自铜人原顶部往北及西北原下,西汉中晚期及东汉时期墓葬比例越大,表明东汉至魏晋以来古人活动区域已逐渐转移到原下(北部),这与“霸城”的兴起、沿用时间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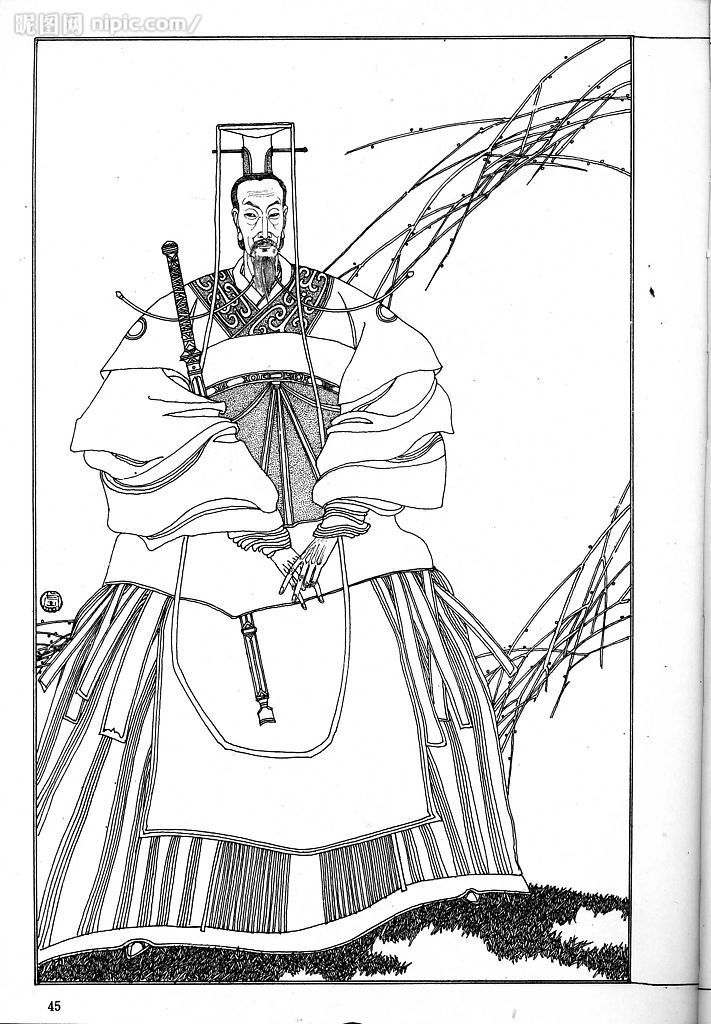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古芷阳(汉霸陵城)”所在地区仅有秦汉文化遗存,至北魏时期早已沦为“废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历史事件不当在此地发生,尤其是赫连勃勃绝不会在此“废城”旁登基称帝。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霸城”一直沿袭使用,自长安城东出大道(潼关道)途经此地,曹魏时即有“铜人被弃霸城南”事件。[参见《水经注》:“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见蓟子训与父老共摩铜人,曰:正见铸此时,计尔日已近五百年矣。”《汉晋春秋》《后汉书》等文献亦有详载,皆明载发生地是曹魏“霸城”而非“霸陵邑(城)”。“霸城”还能控制武关道,与正史文献所载地理位置线索相符。可见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霸上”当在“霸城”南部,即今灞桥区新筑陆旗营至谢村一带(坐标N34°20′53″,E109°0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