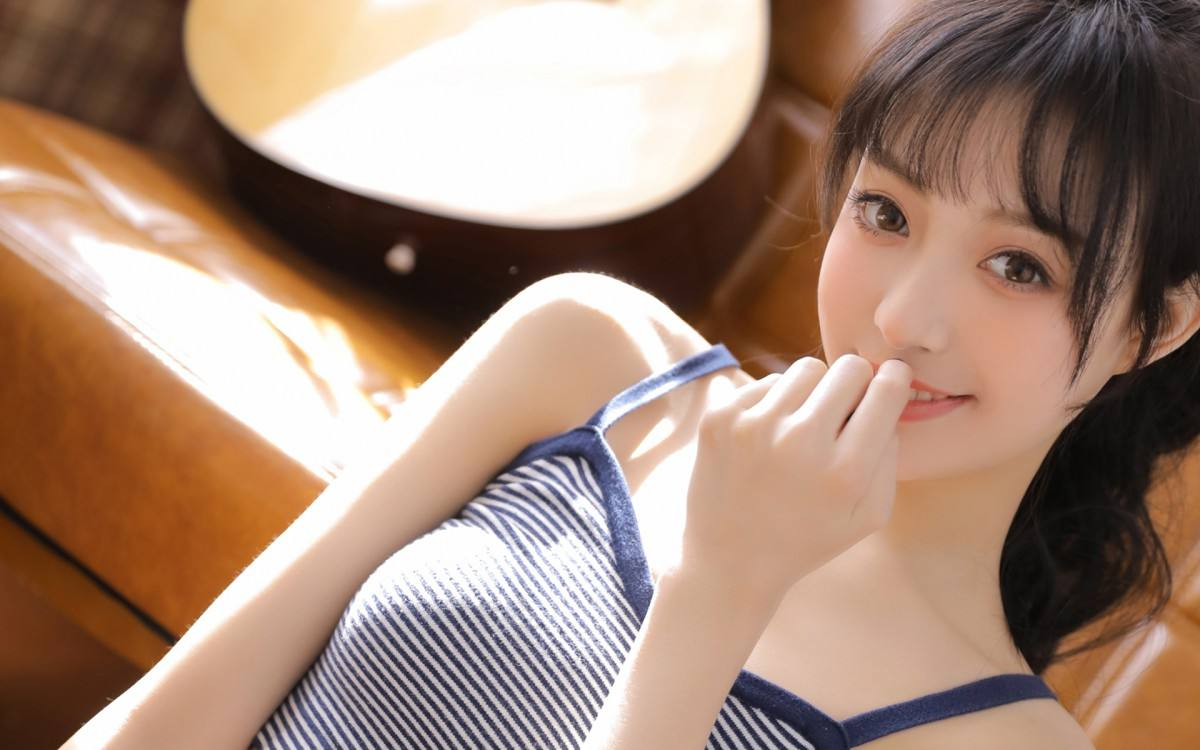林语堂是谁_林语堂生平简介

林语堂(1895年-1976年)福建龙溪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66年定居台湾。1976年在香港逝世。
●本文选自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一书,有删减。
●在该书的《中国人的性格》一章中,林语堂从民主性的角度粗略地勾勒了中华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括了好的品质也包括了一些很糟糕的东西。而且有些特点粗略看来并无大碍,甚至会被误认为是优点,很值得细细地探究。
●依照林语堂的看法,中国人公认的“遇事忍耐”、“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思想就很要不得。在中国人中,这种品质被过分地发展了,从而演变成为一种“恶习”,对暴政的屈服和逆来顺受的普遍心理,将中国引入了一个更为痛苦和艰难的境地。
●林语堂又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另两个特点:消极避世和超脱老猾,并对它进行了深入分析。“消极避世”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的弱点及缺陷;“超脱老猾”应该是一种较之“消极避世”更为“高明”的方法,故而大都掌握在阅历丰富、世故老成的人手中,是一种麻木不仁和自私心理的体现。

中国人的性格
文|林语堂
◆老成温厚
“性格”一词是典型的英语词汇。在理想的教育和人格培养中,除英国人外,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这样重视性格的培养。中国人似乎对性格过于关注,以致于认识不到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还有任何别的东西。
这种陶铸性格的理想模式,即对世俗的欲望不存在任何非份的妄想,不卷入任何宗教侈谈的理想模式,通过文学、戏剧、谚语,一直渗透到最下层的农民之中,给他们提供生存下去的理论根据。
英文中“性格”一词,意谓力量、勇气、“有种”。偶或生气、失望,也只是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而汉语中的“性格”一词则使我们联想到一个老成温厚的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安之若素,不仅完全知己,而且完全知彼。
宋代的哲学坚信理智可以压倒感情,控制感情,自认理智由于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于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可以调整自己、压倒对方,从而取得胜利。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中华民族,并试着描绘其民族性,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1、稳健 2、单纯 3、酷爱自然
4、忍耐 5、消极避世 6、超脱老猾
7、多生多育 8、勤劳 9、节俭
10、热爱家庭生活 11、和平主义
12、知足常乐 13、幽默滑稽
14、因循守旧 15耽于声色
总的来讲,这些都是能让任何国家都增色不少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品质。
(我没有将“诚实”包括在内,因为全世界的农民都是诚实的。中国商人的所谓诚实只不过是用土办法做生意的副产品,是占主要地位的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的产物,如果把他放到一个沿海城市,他就会大大失去那种纯朴的诚实,变得与华尔街的股票买卖经纪人那样不诚实。)
以上这些特点,某些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恶习,另一些则是中性的。这些特点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
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
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忍耐性又可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
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情的代名词;多生多育对民族来讲可能是美德,对个人来讲却又可能是恶习。
但所有这些品质又可归纳为一个词“老成温厚”。这些品质都有消极性,意味着镇静和抗御的力量,而不是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
这些品质是以某种力量和毅力为目标而不是以进步和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的品质。这是一种能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获得宁静的文明。
如果一个人安贫乐道,他就不可能理解那种富于青春活力的要求进步、要求改革的热情。这是一种古老民族的古老文明,这个民族知道生活的意义,不奢求不可企及的东西。
这种中国理性的崇高地位使中国人失去了自己对事物的希望与欲念;理性使他们意识到幸福是无法获得的青鸟(青鸟,在西方文化中为“幸福之鸟”),于是便放弃了这种追逐——正如中国俗语所云“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时他们便发现幸福之鸟原来已在他们自己手中,在方才对想象中的鸟影进行激烈追逐的过程中,它几乎被扼致死了。
如此,便应了一位明代学者所言,“丢一卒而胜全局”。

◆忍事遇耐
让我们列举三个最糟糕最昭著的特点,并看看来龙去脉,通事忍耐,消极避世和超脱老猾。我认为这些都是文化与环境影响的结果,并不一定是中国人心理构造的必然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是由于我们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与社会中并时时受其影响。
自然可以认为,如果消除这些影响,那么这些品质也会随之削弱以至灭亡。
遇事忍耐为中国人的崇高品德,凡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这种品质走得太远,以致成了中国人的恶习: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他们似乎认为这些也是自然法则的组成部分。
在四川的一些地方,人民已经被提前征收了今后30年的赋税,但是他们除了私下在家里发出几声别人似能听见又听不见的咒骂外,再无任何有力一些的反抗。
与中国人的忍耐相比,基督教的所谓忍耐似乎是易怒,而中国人的忍耐有如中国景泰蓝一样举世无双。世界各国的旅行家们蛮可以带一些中国人的这种忍耐回去,像景泰蓝一般赏玩,因为真正的个性是无法模仿的。
我们屈服于暴政和敲诈勒索犹如小鱼投入大鱼之口。
或许我们对苦难的承受力小一些,我们的苦难就会少一些。然而这种对污辱的承受力被赋予了忍耐的美名,又被儒家伦理学谆谆教诲为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我并不是说这种道德不是中国人的伟大品质,耶稣说,“为温顺者祝福吧,因为他将继承整个世界。”能否继承整个世界我没把握,但中国人的忍耐使我们得以继承并管理着半个亚洲大陆却是真的。
中国人把忍耐作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并有意识地反复向后代灌输。谚语“小不忍则乱大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消极避世
如果说在遇事忍耐上中国人是举世无双的,那么在消极避世上中国人的名声就更大了。这一点我认为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在一本英文经典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布朗的母亲在他临行时嘱咐他要“抬头挺胸,坦率回答别人的问题”,然而中国母亲与儿子分别时通常的嘱咐却是“不要管人家的闲事”。
这恐怕是再明显不过的对比了。这种不同是因为在一个人权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会中,消极避世是最安全的政策,它有一定的吸引力,有西方人很难理解的吸引力。
消极避世也并非人们的自然属性,而是我们文化有意识的产物,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慧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
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换句话说,消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
中国青年与外国青年一样,都有公众精神。中国的那些热血青年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都对“参与公共事业”表示出极大的热忱。
但是大约在25-30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了(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学乖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从而大大有助于他们的老成温厚等文化习性的养成。
这种品德的获得,有些人是得力于聪慧的天资,另一些人则因为自己曾吃过一两次亏。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
消极避世的“活命价值”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个人的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就有相当的危险。
我们有两位胆子最大的记者,邵飘萍与林白水,1926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于是其他记者自然很快就领悟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变得“聪明起来”。中国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像中国所有的开明绅士一样,像西方外交家们一样,这些记者一般不对人生大事作任何评论,特别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像他们那样,对此感到自豪。
中国一家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日报,《申报》,以前曾以自己的编辑方针出名,并乐此不疲,即——
1、登载国外而非国内之事;
2、处理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之事而非眼皮底下的问题;
3、讨论一般而非具体的问题,如“勤奋的重要”、“真理的价值”等等。
然而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有参与精神,那是在个人权利有保障的条件下,他只要注意不犯诽谤罪就行了。然而没有这种保障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
换言之,消极避世并非一种崇高的道德,而是一种在没有法律保护下的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它是自卫的一种方式,我们培育这种品质,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

◆超脱老滑
一位超脱老猾者是有许多生活阅历的人,他是实利主义者,麻木不仁,对进步持怀疑态度。超脱老猾的最大优点是能使人老成持重,性格温和;持这种性格的老年人也往往能使许多女孩子倾倒,从而被选作丈夫。因为假如生活能教给人们什么的话,那就该是和蔼温良。
超脱老猾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结晶,它的最大缺点是与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相抗衡。它击碎了人们任何改革的欲望,它嘲笑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它徒劳无益,它使中国人失去理想,不去行动。它能神奇地将人们的活动限制到消化道以及其他简单的生活需求的水平上。
孟子是一个伟大的超脱老猾者,他宣扬人类主要的愿望是吃喝与女人,或者说是滋养与繁殖;已故黎元洪总统也是千位了不起的超脱老猾者。他宣布了中国政治哲学很受人欢迎的格言,也是解决所有中国的党派之争的良方:“有饭大家吃”。
麻木不仁与实利主义的态度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精明看法之上的,这是只有老年人与古老的民族才能有的态度。这种态度,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可能懂得,正如西方年轻的种族不可能理解一样。
有人说人过40就变成了一个无赖,不过我们确实是岁数越大越不要脸。20岁的年轻姑娘很少为钱而结婚;40岁的女人则很少有不为钱而嫁人的,她们或许称之为“平安稳妥”。
希腊神话中的一段故事也许不无寓意。故事让年轻的伊卡罗斯飞得很高直至装在身上的蜡翼遇热融化,他也坠海而死;老父亲代达洛斯则飞得很低,安全抵家。一个人随年龄的增长,会发展一种低飞的才能。理想主义被冷静、平庸的见解改造,被金钱观念改造。于是,现实主义就变成了老年人的特点,理想主义则成了青年人的特点。
中国人极少斗争,也极少反抗。这就发展了某种平静的心灵,使得人们能够忍气吞声,并与自然和谐一致。这也发展了某种防御策略,这种防御策略比进攻策略还可怕。
你到一餐馆就餐,饥肠辘辘,饭菜却迟迟不来,你可以再唤饭店的伙计。如果他态度粗暴,你可以找饭店经理发点脾气。但是如果他嘴上非常文雅地说:“来了、来了。”但是脚上却一动不动,你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做点祈祷,或者也非常文雅地骂几声。
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国人消极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领教最多的人才最能欣赏,这就是超脱老猾者的力量。
据《吾国与吾民》

《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于该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文化等诸方面写得非常幽默、非常美妙,并与西方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等作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所以自1935年由美国纽约约翰·戴公司出版以来,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被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等名士推崇备至,曾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
阅读此书之前,很有必要了解一下作者当时的写作动机和所处的时局——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动荡的、混乱的,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显得模糊而朦胧,让人无所适从。
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赛珍珠序),林语堂也是这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看到当时的中国“无疑是这个地球上最混乱、最受暴政之苦、最可悲、最孤弱、最没有能力振作起来稳步向前的国家”。
当时从个人和周围人群对中国命运的焦虑和担忧中,林语堂却又以崭新的理论,探究了潜在和必然的希望,断言了中国是伟大而不会轻易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