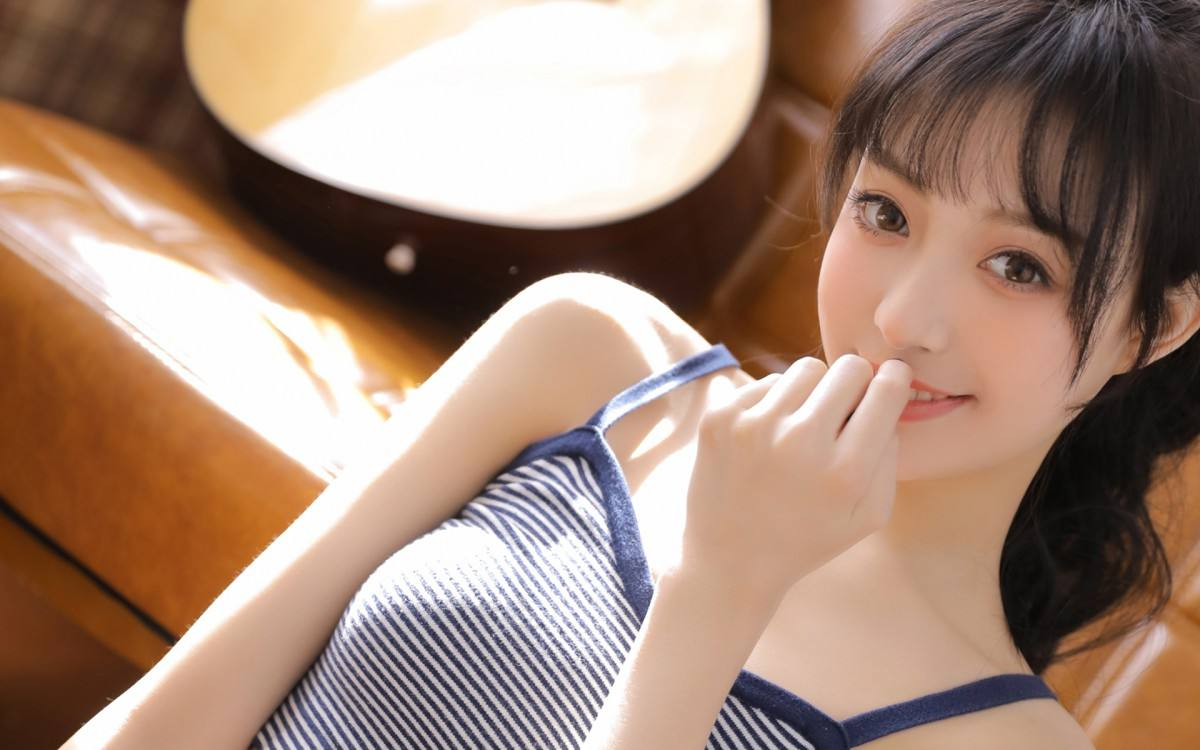沈从文是谁_沈从文的生平简介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1902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西部的凤凰县,他在兄妹九个里排第四,在男孩里排第二。凤凰在民国以前称为镇筸,是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区设立的驻防单位,曾经出过很多著名将领。沈从文也生在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出身自曾国藩湘军,做过贵州提督,他的父亲参加过大沽口抗击八国联军战斗,组织过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读书识字的母亲,给了沈从文主要的早期教育。
沈从文在家乡凤凰县生活了十五年。凤凰这个地方,对沈从文的写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早期生命体验奠定了一个人的经验和情感模式,怎么高估都不过分。凤凰为沈从文提供了密度特别大、但也可以说特别不正常的经验。那里的自然风光美丽幽静,生活着多个民族,沈从文的母亲是土家族人,祖母是苗族人。那里的文化也多种多样,有近两百年的绿营兵制度。军事习惯和多民族世俗生活交织渗透,平常的凤凰是平和安详的,偶尔会出现原始的暴力冲突。而沈从文生长在清末的乱世,从小目睹的是血腥多变的动荡和屠杀。他在幼年时就看惯了杀人,上学放学路上,随处可见尸体,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走过的每一寸土地,脚下都是血”。在回忆录里,他写过“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是他的父亲和叔伯”这样凄惨恐怖的场面。
在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人情里,沈从文发展出特别敏感的感官能力和超人的记忆力、想象力;而乡民的蒙昧、军阀的残酷,又让他生出了沉痛感和悲悯情怀。这种对抗性的记忆来得太早太强烈,在写作中,他总是在潜意识里回避这样的心理创伤。他会用许多东西,比如美丽的女性形象、质朴的家乡风俗,来抵挡真实世界的残酷。这成为了沈从文小说里的重要基调。
因为家境败落,沈从文高小没毕业就参军做了负责抄写的文书员,从此过上了漂泊生活,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一路上,他见识到了更复杂的风土人情,也目睹到更多的暴力凶杀,在一年里,他亲眼看到了七百多次处决。这支部队的结局也很惨,在一次突袭里全军覆没,沈从文认识的人全部被杀,他是因为留守总部才逃过了一劫。
十九岁这年,沈从文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到北京去读书,他说“知识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决心“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他之前受的教育,除了学校里的一点儿,就是跟随舅父学过古诗古文,在军队里看了很多古籍和一些新杂志,再有就是他的书法在当地很有名气。离乡前,他把名字从沈岳焕改成了沈从文。
那时当北漂,一点儿都不比现在容易。沈从文去北京投奔他的大姐,发现大姐夫大学毕业好几年都找不到工作,正要回湘西老家去。一开始,他在燕京大学旁听,但根本没法通过入学考试。在和文学青年的交往里,他产生了写作欲望。想要写小说,他不仅要学新式标点,还要从头学白话文。在四处投稿失败后,沈从文的生活变得极度困窘,用他的话说,就是每天要想尽办法,才能“找些东西来消化消化”。这时候,年轻的沈从文引起了著名作家郁达夫的注意,又得到了徐志摩等名家的帮助。
1926年,在来北京的第五年,沈从文出版了第一本书,收录了他此前的小说、散文和剧本。1928年,他去了上海,和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编辑文学刊物,自办出版社。三个没有财商的文艺青年创业,当然失败得特别快、特别惨。不过,在这一年,沈从文发表了70多篇作品,出版了近20种单行本。其中的短篇小说《柏子》,被公认为是他写作成熟的标志。这篇小说写的是在湘西的河上,有个叫柏子的水手,与沿岸一个妓女两情相悦,但只能一个月欢会一次。沈从文用既细腻又奔放的笔法,写出了他们单纯短暂的快乐和生活漫长的艰辛。这是他最熟悉、也最热爱的生命。
在上海时,沈从文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生活,由于出版社倒闭欠债,他的经济又变得难以支撑了。1929年8月,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破格聘请沈从文任国文系讲师,主讲新文学研究和小说写作。这一年,沈从文二十六岁。根据胡适的回忆,沈从文是全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但对沈从文来说,教书的原因是写作没法支撑生活。在学生里,有他日后的妻子张兆和。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是流传至今的民国佳话,他们的两地书信也成了文学经典,我就不具体介绍了,但是,后面的话题里我要补充一点:这对传说里的神仙眷侣,婚后感情并不平坦,其中的波折和纠葛,也影响到了沈从文的写作。
抗战爆发前,沈从文先后在武汉、上海、青岛、北平等大城市间奔波。在武汉大学任教时,他痛苦地发现,住处不远就是刑场,许多死囚都是十八九岁的男女学生。他当初离开湘西,就是为了摆脱这样的残酷场面,然而此时的中国,到处都是恐怖气氛,他的朋友张采真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胡也频死于上海的“二七惨案”。
1932年,沈从文出版了《从文自传》,讲述他二十岁到北京之前的经历,以及在湘西的种种见闻。虽然篇幅短,但这本书是20世纪最杰出的文学传记之一。它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揭示了沈从文产生自我意识、形成个人追求的过程。从此,沈从文的个人风格全面确立起来了,他当时自豪地说,“我的工作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将会传播得很久很远。”这一点,他做到了。
这个时候,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爱情,他们于1933年订婚,一起前往青岛生活。在青岛,沈从文写出了他的代表作《边城》。这篇小说的主线,是湘西小城里一个撑渡船的女孩翠翠和船总家两兄弟的爱情故事。沈从文以乡间的正直淳朴,反衬出城市文明的堕落侵蚀。《边城》是沈从文最饱满、最流畅的语言状态,在此之前,他的文风缺乏节制,后期则变得有些晦涩。
1934年,沈从文返回了一次家乡。一路上,他亲眼见到湖南经过战乱后的巨变,一切已经物是人非。当时的中国农村,连中小地主阶层都普遍破产了。沈从文意识到,《边城》的浪漫唯美,不能应对正在发生的深刻剧变,用他的话说,这是一次“彻悟”。他根据这次见闻,完成了《湘行散记》,并开始酝酿长篇小说《长河》。同时期,还发表了大量的政论类文章。
1937年北平沦陷,沈从文和北京的一批高校教师撤离南迁,1938年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张兆和也带着两个孩子绕道香港到达昆明。在抗战时的昆明,这些名教授们生活都很贫困,但也共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选择到北大任教,在写作的同时,还担任副刊编辑工作。在1947年,他发表了最后的两篇小说,从此,由于历史和局势原因,他很难再继续文学创作了。
沈从文就是那种既拥有绝世天才,又肯付出超常努力的人。他有特别强大的创作能量,从步入文坛起,沈从文就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冲动,尝试过各种文学样式,是民国时期最多产的作家,他平均每年都发表几十篇小说,《沈从文全集》有上千万字。放在西方艺术家身上,在这样动荡贫困的生活里保持如此高的创作密度,会被形容成是野兽一样的体力和生命力,但是沈从文不仅身体差,写作速度也不快,而且还总是反复修改,不足七万字的《边城》,他整整写了半年,保持产能的办法,只有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沈从文常流鼻血,流起来就止不住,有时候会一直流到晕倒,趴在沾着鼻血的手稿里,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
湘西人有种做事情必须要做出名堂的狠劲,这在当地称作“霸蛮”,沈从文则说自己是“耐烦”,就是能忍耐各种烦恼。他一再对学生说,不要相信任何天才的说法,“这个世界上只有忍耐”,能够耐心地完成一份工作的人并不多。他评价自己的小说成就,也只是觉得比别人要认真,所以才会写得好一些。沈从文小说中细腻精准的效果,确实需要反复打磨。
沈从文给人的印象是温和腼腆,说话声音很轻,总是在微笑,但他的性格又特别坚毅倔强,按照巴金的话说,是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他做事。改行以后,他的生命能量也没有停歇,做了大量没人愿意搞的琐碎工作,写出了有学术奠基意义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为了一个领域内的文物专家。他说,开辟新工作是极有意义的,精力旺盛是条件之一,更重要的是学习的勇气。沈从文的文学事业,是由强烈的生命能量和坚强的自我意识支撑起来的,他的生命追求就是必须把人生投入到具体事业中去。
在情感上,沈从文对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倾注得最多,从另一面来说,也就一直没有形成超越世俗的深刻思想。沈从文是新文化运动里第一个描写普通人生活的作家。当时,其他代表性的作家对于民众的刻画,大多采用知识分子视角和批判思维,最杰出的就是《阿Q正传》了。
这也不能说就是优越感,在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普遍觉得自己应该肩负起引领者和启蒙者的责任。沈从文却将情感和立场完全放在社会底层,他说,“我对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他觉得,普通中国人一直在庄严地承担命运,却始终被排除在历史书写之外,文化人没有资格可怜他们,民众精神才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东西。他甚至责备读者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后来选择研究杂项类文物,也是认为这些不起眼的古董里凝聚着过去人民的智慧和审美。在讲解文物时,他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在说到具体细节,比如刺绣用的金线是盲人凭手感从金箔上切下来的,总是让人非常感动。
沈从文的文学世界因为感动而显得有些脆弱,但并不是架空的。在1938年随大学南迁时,他途经家乡湘西,走访了湘西政界首脑,规劝他们终止内斗,共同抗日,安置好转移过来的机关和难民。他的活动对当地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沈从文还尝试从地方和国家关系的角度,改变写作角度。但是,他的文学创作也一直处于这样的局限:他所凭借的,是自己对生命情感的体悟,而他所追问的,则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一种文化的出路,这样的问题需要更深刻的思考才能解答。我们刚说过,他自幼看惯了杀戮,深切地体会到底层民众的悲惨,这使他经常用抒情代替思考,用立场取代批判,有时则是在世俗的佛家道家思想里寻求简易的解脱。比如,他认为中国民众对不幸的容忍态度,有一种同自然相融合的、从容的道理,赞美他们简直比哲学家知道得更多。好在这只是小说的表达,绝圣弃智的观念没有实际的操作方案,无助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此外,我们还要说一下他的个人生活。艺术家的创作来自他的个人情感体验,沈从文尤其如此,这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张兆和在婚姻中为沈从文提供了全面支持,尤其在后半生,家庭对沈从文的保护太重要了。但张兆和又说,她在晚年整理沈从文文稿时,才发现自己对他并不完全理解。如果你对夫妻生活有经验,就知道这话并没什么奇怪的。张兆和这样说,正是因为最后真正理解了她的丈夫。
但是,他们也同样经历过那种感情纠葛。婚后不久,沈从文就爱上了一个年轻女作家。他自认为是美的忠实追求者,在爱慕某个人时就应该向所有人坦白,他称这为“横溢的情感”。这段感情经历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留下了很多痕迹。他有一篇饱受争议的小说叫《看虹录》,讲一个作家和情人的幽会,采用的是心理分析写法,还有很多情爱场面描写,就是在从侧面叙述这段情感经历。在婚外恋终止后,他又写了《主妇》等短篇小说,纪念和感谢张兆和对婚姻的挽救。沈从文承认过,写作《边城》的动机也与这段感情曲折有关。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先搁置八卦爱好和道德评价,主要观察作家如何将情感体验投射到作品上,获得一个阅读小说的新角度。
沈从文的前半生处于不断的地理位移,而且逐渐从文化圈的边缘进入到了核心位置,他身兼大作家、知名教授和文学刊物编辑的身份,同时身处文学圈、教育界和传媒界,如果我们第三次从头翻一遍这本书,从他的经历里还能看出民国文化界的发展变化来。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它在最危急的时期、最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最多的人才,一般的总结是:这是由于西南联大学风非常自由,没有学历的沈从文能被聘为教授,教师们可以自主教学和考试,不拘一格地教育和评价学生。这两点都有道理,但从沈从文的经历看又都不全面。
咱们就先来说说,到底该怎么看待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今天的人容易神化民国的学术学风,其实民国学术一样有许多局限性,派系山头和潜规则并不少。20世纪20年代,北大曾经在两年多里只出了五种著作和一种译著,被称为“学术大破产”,新文化运动也沦为了所谓“新名词运动”。胡适决定聘用沈从文,并不是欣赏他的小说,而是为了破除这种学风。在民国初年,高校聘任教授确实比较随意,这倒不是自由,而是规则没有建立起来,到30年代,已经逐渐有了门槛。当时,胡适聘用沈从文是有很大压力的,但他觉得,当时的中文系教育太偏重考古了,未来必须要同时兼顾历史、欣赏与批评和创作这三个方向,而创作类的教育,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沈从文这样的作家能胜任。
沈从文的教学方法也是无法模仿的,他开写作课,每一讲自己都要先写一篇范文,再在学生的作品上进行长篇批点,经常写得比学生还长,凡是发现有好的学生作品,都会全力向报刊推荐。他的学生、作家汪曾祺说,沈从文一辈子给学生搭的邮费都是一笔可观数字。
沈从文在学术界的自卑心理一直没有消除,很多教师和学生都不掩饰对他学历的轻视。当年在西南联大有个无法考证的段子,说教授刘文典在一次躲避空袭警报时,一边跑还一边挖苦沈从文:“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嘛跑啊!”这件事被如此传播,就是因为有一条学术鄙视链的存在。沈从文在联大应聘时,即使已经名满天下,又有在高校成功任教的履历,还有清华、联大两位中文系主任的极力推荐,也只能由联大下属的师范学院下聘书,在五年后才晋升教授。
但最值得我们尊重的,恰恰是这种不随便破格的规则。正是由于学术界充满了派系和利益纷争,在权力腐蚀下极易腐败,才特别需要不能轻易突破的刚性制度。学术首先要规范,然后才能推行有远见的弹性和自主。联大精神的可贵之处,不是彻底自由,而是在二者之间取得了平衡,达到了最好的效果。毕竟沈从文只有一个,他那种自由的、贴近学生的教学方法也是很难复制的。
最后,我们再看看民国文化界那些不断升级的矛盾。沈从文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大关心政治,总在无意间身陷学术界的纠纷,而这些争斗的性质是在逐渐变化的,他似乎一直没有领悟到背后的真实逻辑。
沈从文和鲁迅代表了中国短篇小说的两个高峰,但他们之间没有私下交往,只有一场误会。在沈从文刚开始文学创作时,丁玲曾给鲁迅写过一封求助信,但有人认错了笔迹,告诉鲁迅这是一个叫沈从文的男人写的,鲁迅为此极为生气,认为他被愚弄了。沈从文性格倔强,也不愿意解释,两个人后来虽然都对彼此做出过很高评价,但不再有私人接触。这些事情只是个人恩怨,也不构成具体伤害,但后来的矛盾,就扩散到整个学术圈了。
1933年,沈从文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上海的一些作家通过取巧获取成功,没想到,这引起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很快,讨论范围就超出了文学创作,参战的人也越来越多,扩大到学术界整体。朱自清说,京派是为学术而学术,海派则是为名利而创作。鲁迅干脆说,海派是商的帮忙,而京派不过是官的帮闲。沈从文根本不懂得,双方的分歧早已种下多年了,只是在寻找一个开战的机会。此后,沈从文的朋友们多次告诫他:多写小说,少写杂文,不要议论时事。
沈从文在学术上不属于任何一派,虽然热爱民众,但不愿意写政治功能明确的斗争题材,到了文学界分裂成左右两个阵营以后,任何一边都不喜欢他,都对他进行批评。当老朋友丁玲指责他与人民脱节时,他还认为这是风格和个性的问题,是由于他“能承受生活的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反抗性”,“不习惯受人管束,也不会管束别人”。当指责声越来越大,比如说他的《边城》居然把地主写得那样善良豪爽,“掏空了阶级属性”时,他不客气地回答:“你们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很容易办,可是我存心放弃你们。”他没有意识到,此时所讨论的已经不是文学了。
沈从文曾经刺痛过郭沫若,一次是评价郭沫若文字不含蓄,不会写小说;一次是说在进步作家中,巴金和茅盾在辛苦的工作,郭沫若只是在走莫斯科的上层路线。我们不能断定,这和郭沫若1948年3月发表的《斥反动文艺》有没有因果关系,但那篇文章决定了沈从文一生的命运。郭沫若写道,沈从文的小说是“文字上的春宫,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活动”。这个时候,文艺批评已经成为了政治定性,将导向现实中的打击。后来,在沈从文陷入精神危机时,北大学生又把这篇文章抄写到墙报上,造成了他的神志失常和自杀未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是文化不断被政治所干预、所吸收的过程,也开启了下一个时代的文化局面。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第一,他出生于偏远的湘西小城,少年时经历了斑斓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异常残酷的杀戮。他以小学文化闯荡中国文坛,不仅成为最高产、最受欢迎的小说家,还成为西南联大教授,教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第二,支撑沈从文写作的,是他自称为“耐烦”的强大意志力和必须有所作为的生命追求。他热爱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崇拜美与质朴的情感,但不善于进行深刻的、批判性的思考。第三,在沈从文身上,我们还能看到民国教育界、文化界的变化:民国学风不仅有局限,也有壁垒,沈从文的破格,始终是、也应该是一种例外。同时,文化界的纷争,逐渐从个人纠纷变为派系之争,最后彻底进入政治话语体系。
文学史和其他历史一样,会在长时间停滞后,像江河的激流一样,突然开始快速地发展,体现到个人身上,就是在一个时期里连续遭遇重大的命运转折。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回忆,在1948年夏天,他问过父亲:有人说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我看你比不上他。沈从文认真地回答说:没错,我确实比不上,许多事情耽搁了我,我以后要好好赶一赶。历史没有给沈从文这个机会,但是,他已经用一生努力过了。我们的时代机会比沈从文要好,那1%的天才,我们和他比不了,而99%的努力和顽强执着的“耐烦”精神,我们能不能也赶一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