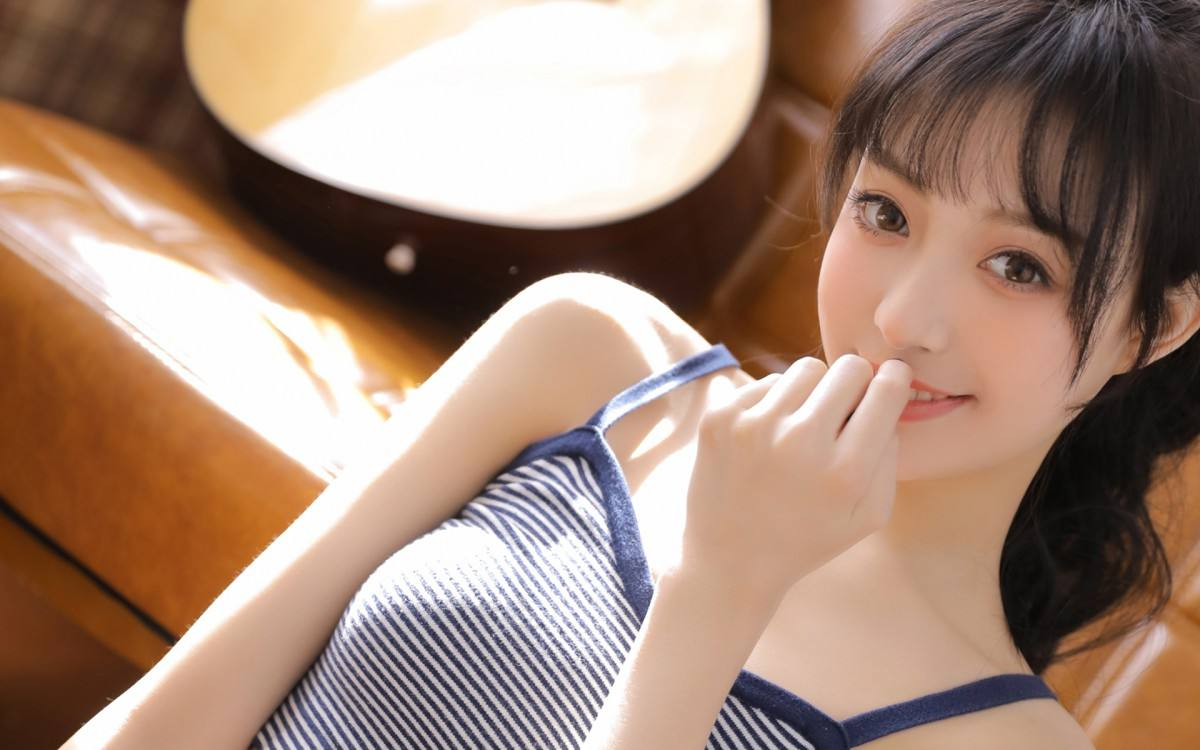汪曾祺是谁_汪曾祺的一生经历
1946年,上海。
26岁的汪曾祺,刚刚从西南联大毕业,迈向社会。
他青春勃发,踌躇满志,却辗转多方,屡屡碰壁,始终找不到一份工作。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也落魄到了极点。
对于这段日子,他曾半戏谑地说,那时口袋里的钱时不时要摸一摸,出门就害怕自己会摔跤,万一把人家的橱窗摔破了,该拿什么来赔呢?
他一度认真地想过赴死。
恩师沈从文得知后,写信把他骂了一顿:
“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于是,汪曾祺不怕了,他不停地写啊写,写秃了数不清的笔,写白了两鬓。
但一直至60岁的前夕,他还是没有看到“出息”二字的任何迹象。
1939年6月,从未出过远门的汪曾祺背起行囊,离开家乡高邮,由上海坐船经香港,再从越南坐滇越铁路火车到了云南昆明。
他千里迢迢慕名而来,只为了一个目标——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是战时的一所临时性大学,集结了一大批被迫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的知名学者教授。
其中,汪曾祺入读的中文系更是堪称王者配置,神仙打架现场。
有上课抽烟且也允许学生抽烟的闻一多,在吞云吐雾中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讲屈原:“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有酷炫狂霸拽的刘文典讲庄子,第一节课就先来一句霸气侧漏的开首语:“《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还有讲古文字学的唐兰,讲《花间集》,但他基本不讲,只用无锡腔“吟”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
跟着这群极具个性的老师学习,汪曾祺也表现得相当有个性,该上课上课,该逃课逃课。
上杨振声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他写了一篇精彩的短报告,当堂获得了期末免考的特权。
上沈从文的小说写作课,他的一篇习作更是获得了120分(满分100)的高分,让沈从文欣赏不已,逢人便夸,到处推荐他的文章。
但是,并不是所有老师都喜欢汪曾祺,比如朱自清就对他印象不佳。因为朱自清讲宋诗课,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诵,还有月考、期考,而汪曾祺老是逃课缺课,所以朱自清就不大喜欢这位不用功的学生。
汪曾祺逃课干啥?
他有两大消遣:一是“泡图书馆”,二是“泡茶馆”。
汪曾祺极爱涉足昆明的各色大小茶馆,因为茶馆里什么样的浮世万象都能见到,像一个万花筒,正合他好奇的口味。
他曾去过一家又脏又乱的小茶馆里喝茶,在一面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墙上发现了一首诗:“记得旧时好,跟随爹爹去吃茶。门前磨螺壳,巷口弄泥沙。”这使他大为惊讶,这首诗真实自然,诚挚动人,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诗”。
汪曾祺刚到昆明的头两年,除了正常的生活,还得时时应付突发情况——“跑警报”,应对日本飞机的轰炸和骚扰。
警报一响,大家就拔腿往郊外跑。有人每次跑警报,都随身携带一个装情书的小箱子。不过,也有个女同学从来不跑警报,反而别人一跑,她就去洗头,因为这时没人排队。还有一个很爱吃冰糖莲子的广东同学,一有警报,就把莲子拿去锅炉火口煮,等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煮好了。
汪曾祺则最喜欢往松林的方向跑,那里“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而且还能在树下捡到成熟的松子,嘎嘣嘎嘣咬着吃,不愁饿着。
当初,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冲着沈从文来的。考入联大后,他追随沈从文多年,最终成为了沈从文最得意的学生。
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小说给沈从文批阅,文中有两个人物的大量对白,对话很美,很诗意,有哲理。
但是,沈从文看了以后却告诉他:“你这不是人物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并建议他说,对话“要贴到人物来写”。
这句教导对汪曾祺的写作影响很大,从此他知道了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应尽量朴素,言简意赅。
汪曾祺在昆明所写的稿子,全是由沈从文细心修改,然后亲自寄出去,推荐给相熟的报刊发表。
沈从文还说,汪曾祺的小说比自己要好。他在给施蛰存的信中特别提到:“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两人之间的相处很随和,沈从文不以师长自居,汪曾祺也不以学生而自卑,他们像朋友一样亲近。
有一天晚上,汪曾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从文从一处演讲回来经过,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发现是汪曾祺,便和两个同学把他扶回到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汪曾祺才醒过来。
还有一回,汪曾祺因为牙疼肿着个腮帮子去沈从文家。沈从文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转身出去买了几个大桔子,抱着回来了。
汪曾祺毕业后去了上海,因为找不到工作心灰意冷。沈从文得知后来信,一方面鼓励他,一方面设法帮他找工作。
就这样,沈从文托李健吾帮助,汪曾祺去了一所私立中学教国文。
后来,因为未婚妻施松卿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当助教,汪曾祺也去了北京,但仍然没有工作。最后还是由沈从文设法帮他在历史博物馆谋到了一个清闲的办事员职位。
之后十几年间,汪曾祺辗转去武汉教书,又回到北京负责几个刊物,做编辑,日子显得过分平淡,在汪曾祺人生履历上,始终没有出现当初沈从文断言的“手中有一支笔”“必有大成就”的结果。
对此,沈从文看在眼里,忍不住为他这个学生打抱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
再后来,汪曾祺连平淡的日子也过不成了。
1958年,因为所在单位《民间文学》右派指标有余,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60年代,他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又卷进了新的动乱中。
在岁月的淘洗下,汪曾祺已经不会像26岁那年一样“哭哭啼啼”,无助到闹自杀了。他已经能玩笑地说:“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在农科所,他负责给土豆画图,他画得津津有味:“到了马铃薯逐渐成熟——马铃薯的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我就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了,想画得不像都不大容易。画完一种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
在这种境遇里,沈从文一如既往地安慰汪曾祺,仍然鼓励他不要放弃写作,尽管他自己已经不写了,可他还是很看好他的学生。
“可是我却依旧还是想劝你在此后生活中,多留下些笔记本,随手记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时,还是十分有用。……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完成这个愿心!”
“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
又说,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我这个老师和三姐(张兆和),“事实上还有(黄)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
汪曾祺又拿起了笔,他那已经不再清亮的双眸中,忽地流淌过故乡高邮清亮亮的水,芦花荡中芦花才吐新穗,两支浆飞快地划过,惊起一只青桩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他想起了读书那年,老师说过的要语言“贴到人物来写”,想起了茶馆中听过的各色故事,又想起了少年时为躲避战火随父在乡间小庙居住的经历,一个散文诗一般的故事缓缓地浮现在他的笔下。
这个不过一万二千字的故事最后命名为《受戒》,是关于小人物、小事件、小生活的故事,完全没有关注到彼时主流的“宏大主题”“宏大叙事”。汪曾祺写完后自知不合主流,所以并没有奢望发表,只给一些朋友和同事传阅了初稿。
令人意外的是,在主流评论界保持沉默的情况下,这个小故事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一个公社书记私下对汪曾祺说,他们公社开会时有两位大队书记一边开会,一边默写《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
作家阿城说:“有一天在朋友处翻旧杂志……忽然翻到80年一本杂志上的《受戒》,看后感觉如玉,心想这姓汪的好像是个坐飞船出去又回来的早年兄弟,不然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工农兵气?《受戒》没有得到什么评论,是正常的,它是个怪物。”
《受戒》发表于1980年,是汪曾祺的成名作,而这一年,他已经年届六十。
第二年,汪曾祺又写了一篇《大淖记事》,依然是水乡上小人物的小故事,依然不过一万二千字,依然出奇地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作家杨沫说:“读了《大淖记事》这样的作品,使人仿佛漫步在春天的原野上,嗅到一阵阵清新温馨的花香。”
这阵“清新温馨的花香”,冲散了空气中充满“伤痕”与“反思”的浓烈气息,沁进了人们的心扉,同时也迅速让汪曾祺大红大紫,一个被埋没了多年的作家浮出水面。
早在汪曾祺成名之前,沈从文就坚信过他的学生终将“大器晚成”,他说:“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当初,有人劝汪曾祺写点宏大的文章,汪曾祺想了想,摇了摇头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汪曾祺作品中处处透露出面对生活的独特可爱态度,于生活亦处处有洞见。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但他却宁可去逛逛菜市场。他说:“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他觉得一个人的口味最好要杂一点,最好能多听懂几种方言,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要知道生活本来是很好玩的。
对生活兴趣很广的汪曾祺,便把目光都流转在人间草木、四方食事、天涯游子、故人往事上。
有人问他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他说:我东瞧瞧,西看看,不知怎么地就成了作家。
后来,又有人问他为什么写作,他写了一首四言诗回答: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汪曾祺觉得一个人不能从早写到晚,不然就跟一架写作机器无异,得找点事情消遣消遣。他为文之外的爱好有三个:写字、画画、做饭。
他的字和画都属于自娱自乐,大多写意,没有受太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主要是好玩。
他曾给好友邓友梅画过一幅梅花作为结婚贺礼,画的是铁干梅花,树干树枝都是墨染,梅花却是白色的。他随画夹的字条说明“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要好友猜那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
结果,好友夫妇俩猜了两月都没有猜出来,有天见面了,汪曾祺得意地笑笑,说:“是牙膏!”
汪曾祺还爱做饭,并且常常做饭,家里的两顿饭常年都是他做的。拿手菜是“煮干丝”和“酱豆腐肉”,自创菜式有“塞馅回锅油条”和“蜂蜜小萝卜”。
他经常忙活了一通把菜都弄好以后,端上桌,一般只是每样菜尝两筷子就不多吃了,然后就喝酒、聊天,所以他自称:“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
比起做菜,汪曾祺更加“会吃”,说是作家里最会吃的也不为过。他还吃出了点人生道理:“许多东西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儿来了。”
别人夏天啃西瓜,最多嚷嚷一句:“啊!这瓜真甜啊!”而汪曾祺说:“先将西瓜泡在井里,捞起后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他迷恋昆明的糖炒栗子,称之为“天下第一”,并列出了三条理由:第一,栗子都很大。第二,炒得很透,颗颗裂开,轻轻一捏,外壳即破,栗肉迸出,无一颗“护皮”。第三,真是“糖炒栗子”,一边炒,一边往锅里倒糖水,甜味透心。在昆明吃炒栗子,吃完了非洗手不可——指头上粘得都是糖。
当然,他最爱的应该要数家乡高邮的咸鸭蛋,他是这么吹捧的:“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1997年5月16日,这个可爱有趣的老头因病去世,临终前他还惦记着,“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26岁那年,恩师沈从文告诉他,“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
是啊,怕什么,但年轻的汪曾祺心里未必有底。
人至中年,为人父后,汪曾祺常写完小说就让孩子们看,结果每个人都说老头子写得不好。
他喝高了以后,才敢为自己反驳道:“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如今,他早已进了文学史,在现当代作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他没有说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