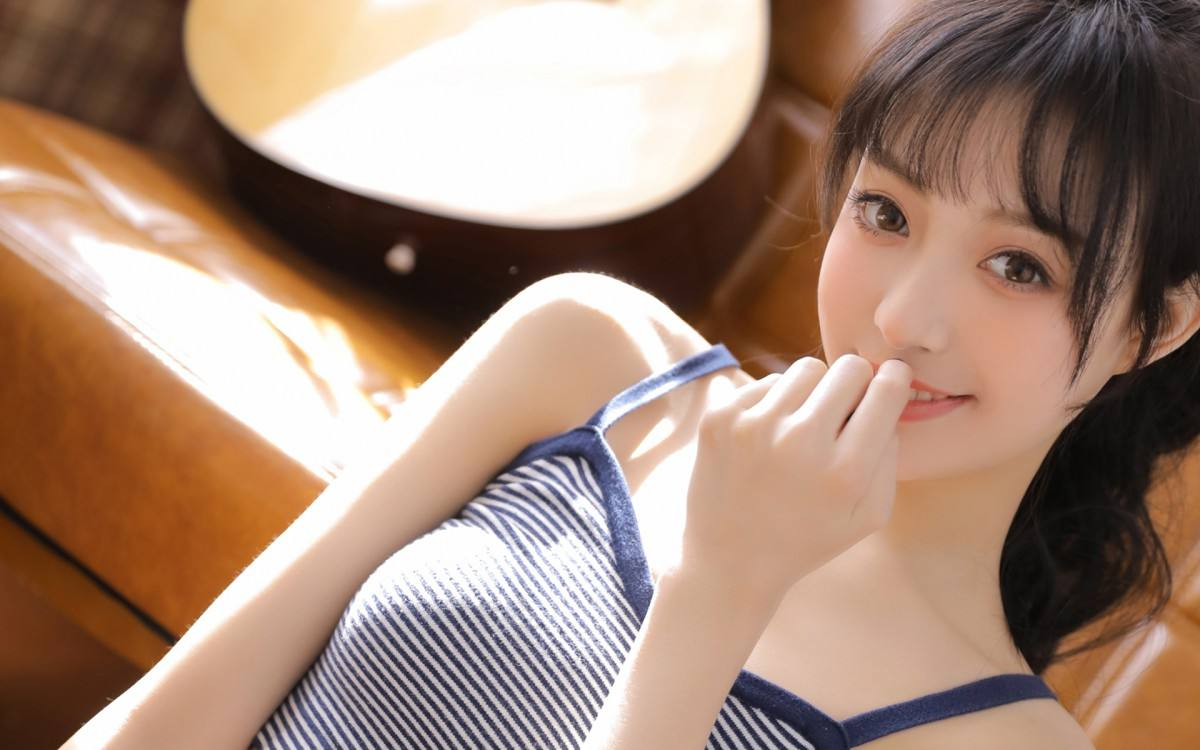张东荪是谁_张东荪个人资料
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辛亥前后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1886年12月9日出生,祖籍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据张东荪手订《增订张氏近世考》记载,张氏祖辈为官宦世家。曾祖父张裴做过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1843年升泰州知州,1853年病逝任内。父亲张上龢(1839—19年),曾先后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张东荪长兄张尔田(原名采田)。在父亲及长兄督责下,张东荪自幼受传统儒学的启蒙教育。1902年左右,张东荪偶读佛经,为其中深奥的思辨玄理吸引,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回忆说:“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趣。”又说:“我在十岁的时候曾信仰过佛教。”早年研读佛经,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一方面养成了他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培植了他苦思冥想的哲学素养,直接促发了他“以为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源不可”的“疑心妄想”。另一方面,为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佛学成为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1905年,张东荪由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他与蓝公武、冯心支同住在日本本乡丸山新町。起初本是佛教信徒的他,与蓝公武时常讨论生死问题,但很快便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并为之折服。他曾说:“我在那时已略略领受西洋哲学的滋味,尤其对于心理学起了兴味。”因此,当蓝公武对他讲“大悟万物唯心的道理”时,他开始产生了一个疑问:佛教所谓解脱或涅槃的境界是否一种心理的变态。
1906年,他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它是综合性的学术月刊,由他与冯世德组织的“爱智会”主办。该刊物以“会合东西各国学者,研究高尚学问,尽人道、洗俗垢,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分社说、学说、科学、思潮、批评、纪事等九个专栏,以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为重心。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心理学悬记》(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二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他还发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仅从《教育》杂志这两期中已可知,张东荪的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接触和掌握了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初步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
辛亥革命
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国。1911年他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曾这样记述自己的活动:“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参加袁世凯先生所组织的政府,我则不愿意参加。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此时梁启超组织进步党,“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式加入该党,亦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但因他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主张又颇相近,故仍被时人视为进步党的骨干。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积极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但他主要是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在《庸言》、《中华杂志》、《新中华》和《甲寅》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仅1913年就达到30多篇),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他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不赞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为此,曾写过许多政论文章进行抨击,深为袁世凯不满。当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后,他先后发表了《复辟论之评判》、《名实与帝制》等文章进行抨击,当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时,张东荪立即发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坚决进行批驳。洪宪帝制复辟破产后,他主张孙中山与梁启超联合,共建中国共和制度,并发表了《今后之政运观》、《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等文章。但因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意气之争”,他的主张不为人注意。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贤人政治》长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仍不为段祺瑞政府所纳。
1918年,新国会举行选举,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由进步党演变而成)企图借机确立在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研究系在新国会选举中惨败。梁、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破灭。张东荪认识到,“立宪派只问政体而不问国体,在表面似乎较革命派为接近一些民主真义,无奈他们只以政府构造上着眼,而忽视关于社会主义全般的义理”,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和研究系今后的出路。1918年底,梁启超决定赴欧洲考察,途经上海时,与张东荪、黄潮初畅谈一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此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张东荪随后也表示,此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要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尽其力量。
自1917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为宗旨。1919年初,他把《学灯》由周刊改为日刊;4月又聘请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19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任主编。在创刊号上,亲自撰写创刊“宣言”,发表题为《第三种文明》的社论,并写了长篇读书杂录《罗塞尔的政治思想》,提纲挈领地表明研究系的趋向及其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即要致力于社会的解放与改造,培养“第三种文明”。此后他又在《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新思想与新运动》、《奥斯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评资本主义的办事方法》、《改造要全体谐和》、《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等文章,全面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宣传社会改良。
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回国,与张东荪等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
9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并在《发刊词》中申明:要将基尔特社会主义精神向“实际的方面”贯彻。同时,梁启超、张东荪以讲学社名义邀请英国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陪同他到湖南等省演讲。1920年12月6日,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陈独秀等对此文进行批驳,展开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连续发表《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等文章,进行反驳。1920年12月25日,他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全面阐述了他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1921年1月19日,梁启超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赞同并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并对《现在与将来》作了某些“发明补正”。2月15日,张东荪又作了《一个申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比较正式说明”,系统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说”。1921年9月日,他又创办了《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在《宣言》中,公开宣言:“我们怀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竖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宣言我们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全面提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信仰、研究方向及宣传目的;认定:“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系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确是民主主义思想的究极,而且是社会改造原理最彻底的一个。”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批评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市场越来越小。1922年6月和9月,《社会主义研究》和《改造》杂志相继停刊。
1920年,张东荪等人开始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他自任大学部主任,聘请国内名师做教授,后因经费困难而辞职。对于他在中国公学的情况,他的好友俞颂华回忆说:“他也办过中国公学,他办学的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个特色: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研究的学风。这话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所可惜的,那时经费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时间亦不够长。”在五四时期新旧思潮大论战中,张东荪发表了《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答潘力山君与程耿君》、《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文章,反对章士钊的调和论,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他认为:“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学便是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如要彻底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可。”
所以,张东荪输入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西方哲学。1921年12月在《民铎》上发表《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1922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1923年发表《这是甲》、《批导的实在论》、《相对论的哲学与新伦理主义》、《唯用论在现代哲学上的真正地位》、《伯洛德的感相论》,1924年发表《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1925年译介英国哲学家卡阿著《科学与哲学》,1928年发表《新创化论》等。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而尤其注重于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穆耿的新创化论、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