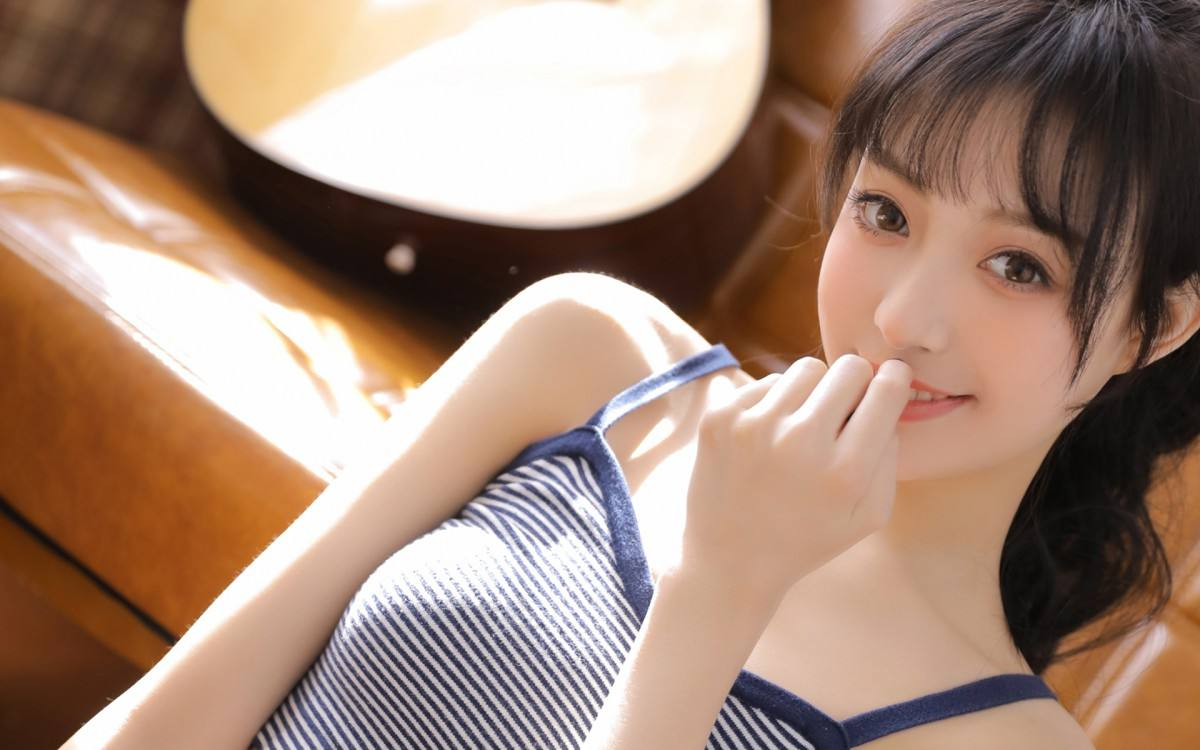萧乾是谁_萧乾简介及作品
1953年春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楼下,萧乾加入了做工间操的队伍,他刚调来不久。
由于腹部凸出,弯腰时,双手怎么努力也触不到地面,校对科的一位姑娘忍俊不禁,冲着文洁若咬耳朵:“你看萧乾那个怪样儿!”
那是文洁若第一次见到萧乾。那时,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人生,将会和这个大作家、大记者绑在一块儿。
感谢世界生了个雪子
萧乾的大名,文洁若早就熟知,高中时读到他的《梦之谷》,她就被深深打动。
二战时,萧乾曾是《大公报》在欧洲的战地记者,他亲历了伦敦轰炸、攻克柏林等重大事件,报道过很多历史性场面。
战争结束,他本可以做收入不菲的香港报人,或是受邀到剑桥大学做教授,但他还是“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刚到出版社时,因为修改一部电影剧本,萧乾很少露面,需要他修订的稿子,都是送到家里。
有一天,文洁若带着苏联小说《百万富翁》上门请教。尽管她曾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有名的才女,但以当时的文字功底,校样改了五次,仍不能付梓。
十天后,她拿到了萧乾润色的稿件,一读之下,如醍醐灌顶,深受启发。
他的才华令她折服,他上班后,她便经常去讨教。
几次相处下来,文洁若发现,萧乾完全没有大人物的架子,他学识渊博,说话诙谐俏皮,对她这个小助编,也给予了足够的耐心和鼓励,这让她非常感动。
随着交往增多,他们惊奇地发现,两人有太多的共同爱好:都研究外国文学,都喜欢罗曼•罗兰、狄更斯,都爱听莫扎特的《安魂曲》。
平静的生活突然漾起微澜。文洁若自幼以书为伴,在这之前,没有一个同龄人能让她产生兴趣。她意识到,在文字上,萧乾是向导,也是知音。
似是心有灵犀,文洁若这边刚刚心动,萧乾已经有了行动——他约她去北海公园划船。经历过三次失败婚姻,他迫切想要一个家,文洁若对学问的专注,他非常欣赏。
约会那天,萧乾还带上了6岁的儿子。不料,他们正荡漾在荷花丛中时,被出版社的同事撞见了。
背地里,同事们纷纷劝文洁若:“一个挨过文坛泰斗痛骂的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前途的,你是个单纯的姑娘,怎么能和他接近?”
何况,他43岁,而她只有26岁;更何况,他还三离其婚,带着个孩子!
对此,萧乾坦诚相告。在《大公报》发表的社论中,他曾抨击过文坛“称公称老”的风气,得罪了郭沫若,被打击批判,不允许搞创作;
至于不幸婚姻,他也毫无隐瞒:“甩过人,也被甩过。正因为走过弯路,所以会更为明智清醒。”
最终说服文洁若的,是她内心的感受:“这腔挚情,一生中只能有一次,不论将来遇到多大的风险,吃多大的苦头,我也豁出去了!”
爱的力量战胜世俗,她决定与他共担命运。 对此,萧乾非常感激。为表心迹,他特意送给她一枚精致的玛瑙胸针,锦盒盖子的背面写着:“感谢世界生了个雪子。”署名:乐子。
雪子,是她的日文名;而乐子,是他的小名。
他请她去看话剧,当剧中人在台上说“我们40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时,他捏了一下她的手,小声说:“我40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我找到家啦!”
嫁给他,就是嫁给宗教
1954年春天,一辆三轮车把文洁若的衣服和书拉到萧乾的家。没有婚礼,没有誓词,也没有通知任何人,但他们两个人都像找到了生命的归宿。
简单的家是那样舒适、理想,萧乾经常愉快地哼起美国民歌《可爱的家》,两个孩子的接连出生,更为他带来极大的快乐。
然而,创作不被允许,内心难免愤懑,文洁若建议他:“去翻译几本书好了,总比虚度光阴强。”
萧乾本来对翻译缺乏热情,看到文洁若业余翻译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受到激励,他也一改懒散,一口气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好兵帅克》等经典著作。
在译著的过程中,他们继续“文字之交”,她在他的译文上贴上小纸条,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则回她一个纸条:“洁若同志,谢谢你的帮助!”
《好兵帅克》出版后,不少人称赞文字幽默俏皮,表达了原著的风韵。
他们互相督促,共同进步。在萧乾指导下,文洁若的文字也变得洒脱,好几位有名望的译者,都对她加工过的稿子表示满意,精准的翻译风格开始显现。
那是最幸福的日子,也是翻译的高产期。工作之余,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带三个孩子去公园游玩,孩子们在笑在闹,他在拍照,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光芒。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1957年,因为两篇文章成为“毒草”,萧乾被打成右派。
困在小小的书房里,他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听到很多右派妻离子散时,他非常惊恐。文洁若安抚他:“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孩子们也不会背弃你,总有一天,你仍将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爸爸!”
不久,萧乾被下放农场。因为是业务骨干,文洁若的饭碗保住了。寡母要赡养,姐姐常年患病需要照顾,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她只有拼命工作,才能撑起这个家。
每天晚上,安顿好老人和孩子,文洁若就在小厨房的案板上工作,一直到凌晨两点。短短一个多月,就突击编好40万字的稿子。
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她说:“我是一只老母鸡,我要把萧乾和孩子们保护在我的翅膀之下。”
和萧乾的通信更勤了,每两三天必往来一次,每封信都编了号。在信中,除了鼓励他、安慰他,翻译英文著作时,文洁若经常大段大段地抄上原文,就译稿征求他的意见。
在农场的大棚里,萧乾一边看菜地,一边为文洁若答疑解惑。北风呼啸的夜里,他写信、读信,看孩子们画给他的小人儿、大苹果。
棚外,漆黑一片,方园几里,阒然无人。多年后,忆起往事,萧乾由衷地说:“1957年的雪子,在我心目中是个超人。”
可是更大的风暴随之而来,这次,文洁若也没有幸免,批斗、抄家成了家常便饭。
萧乾不堪凌辱,多次自杀,她不断给他打气:“只要家里还有一个避难所,哪怕是一个窝棚,只要晚上能躲进去,就能歇会儿,缓过来。”
1969年,一家人下放湖北咸宁,年近六旬的萧乾被当作壮劳力使用。
为了保护他,文洁若一改温和腼腆,变得“越来越凶”,敢和排长吵架。她替他挑50公斤的泥;白天下大田,晚上替他值夜班。
她向老乡买了甲鱼、鸡蛋,把罐头盒改造成煤油炉,在破败的土坯房里,为他开“小灶”。
她在宗教家庭长大,嫁给他之后,他就是她的宗教。
最后一首爱情诗
熬过漫长的黑夜,曙光终于到来。相继回京后,再次提笔,恍若隔世。
房子早被侵占,一个门洞装了门窗,就是栖身之所。斗室只勉强容得下萧乾和孩子们,文洁若把办公室的椅子一拼,以社为家,一住就是十年。
这十年,他们互相促进,译著源源不断,进入新的高产期。直到1984年,他们才有了自己的家,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意,起名为“后乐斋”。
在“后乐斋”,萧乾焕发出新的活力,译新著,整理旧作,他随手写在纸片上的,不论多么潦草,文洁若都替他整理得工工整整。在她协助下,他完成了几十万字的代表作品,其中就有名作《未带地图的旅人》。
萧乾的成就受到重视,担任了重要职务,经常受邀到各国参加文学交流活动。多年农场摧残,导致冠心病、肾结石多病相催,几次住院、手术让他变得更加脆弱。
一次住院时,文洁若怕吵醒他,悄悄坐到洗手间去看书,他一睁眼,看到行军床上没有人,焦急地满世界寻找。几十年患难与共,他一天也离不开她。
1990年,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找上门,请他们翻译《尤利西斯》。此前,他曾想请钱钟书出山,钱钟书笑答:“八十衰翁,若译此书,无异于别开生面的自杀。”
那年,萧乾也80岁了,他同样选择拒绝。这部公认的“天书”,他太熟悉了,“搬这座大山太自不量力”。
文洁若却斗志昂扬,这块硬骨头,她想啃下来。尽管,她也63岁了。
为了说服萧乾,文洁若先翻译了一章。萧乾试阅后,说:“底稿还不错,润色起来不费事。”欣然同意。
从此,“一对老人,两个车间”,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他们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疾病缠身,仍想工作;谈话请短,约稿请莫。”
在他们通力合作下,整整四年,百万字的《尤利西斯》全译本终于完成,那不止是对荒诞20年的补偿,更是他们“献给对方的、最生动的一首爱情诗”。
《尤利西斯》译本在文化界引起轰动,受关注程度远超他们的想象。
人生最后一圈已圆满跑完,1999年,萧乾微笑离世。在留给文洁若的最后一封信里,他说:
“洁若,感谢你,使我这游魂在1954年终于有了个家——而且是幸福稳定的家。同你在一起,我常觉得自己很不配。你一生那么纯洁,干净,忠诚,而我是个浪子。我的十卷集,一大半是在你的爱抚、支持下写的,能这样,不能不感激你。”
把往事折叠好,文洁若开始整理萧乾的书信、回忆录、散文集,马不停蹄。每当她伏案时,“后乐斋”的橱柜顶上,年轻的萧乾正歪着脑袋,笑嘻嘻地注视着她。
相爱相守几十年,一路趟激流,爬危岩,用心如日月。晚年时,文洁若自豪地说:“我一生只做了三件事: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