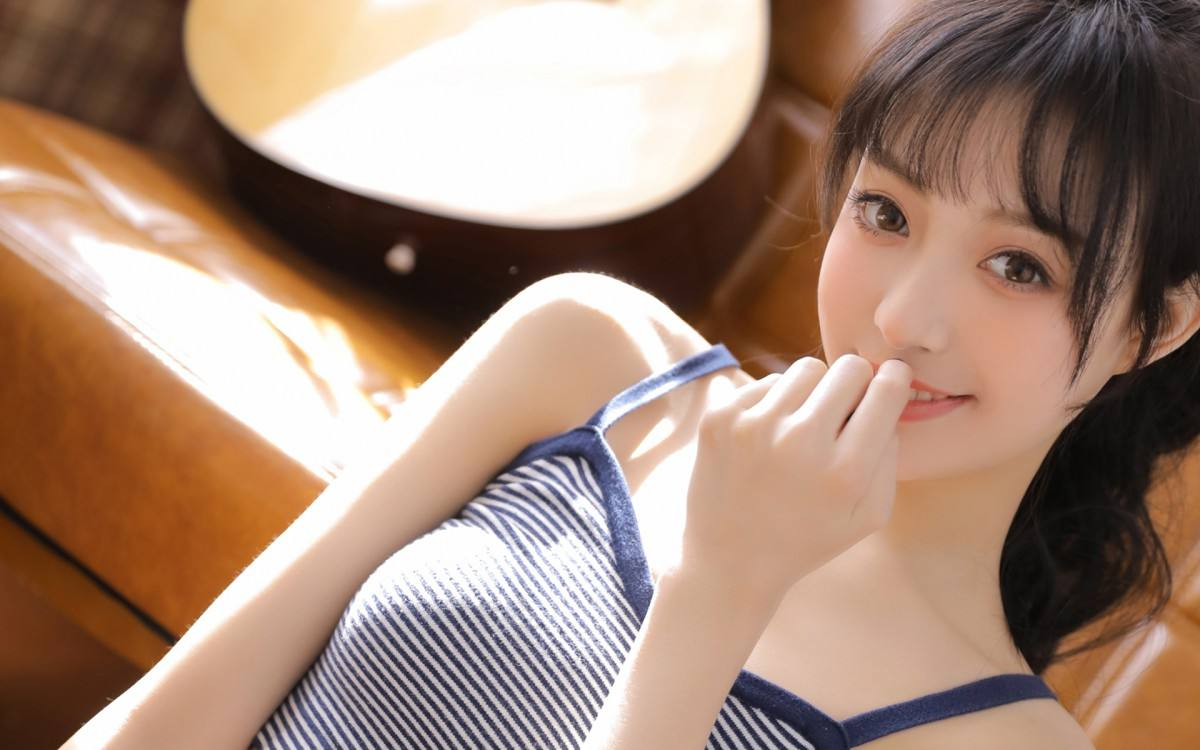安禄山叛乱怎么回事_安禄山叛乱背后隐藏的真相
安史之乱因成为唐朝历史转折的标志而为人们所熟知,通过后人不断的记载和描述,安史之乱的具体情节我们已耳熟能详了,虽然尚有诸多细节需要澄清。我在这里要讲的不是这场叛乱本身的具体情况,而是叛乱背后隐藏的东西,以及叛乱对唐朝此后的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影响等。先谈第一个问题。
安禄山叛乱打的旗号是清除玄宗周边那些扰乱王朝正常秩序的异己势力,他们以时任宰相杨国忠为首。叛军占领洛阳后,安禄山另立江山的意图就变成了现实,他建立大燕政权取唐朝而代之。他起兵所依托的军队首先是盘踞幽州的范阳节度使和治营州的平卢节度使军队,外加河东节镇的兵力,总兵力十四五万人,几乎占十节度使49万兵力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他依靠唐朝的军队进攻唐朝的两京以抗衡王朝,所以叫“叛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人们解释说,是安禄山利用了唐廷给予他的机会,或者叫有机可乘。的确是这么回事,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我这里要说的是他依凭的军队背后的制度,如何导致节度使个人权力的增大,以及制度背后到底反映的是什么情况。
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唐廷已陆续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五府经略使,分布在东北至西南的农耕边缘地带,重点保护以长安、洛阳为核心的中原腹地。防备的对象包括契丹、奚、突厥、吐蕃、南诏等周边各种非汉人的政治势力,突厥、吐蕃、南诏早已建立政权,契丹、奚则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存在。设置十节度使的目的就是防边,这是玄宗沿承前朝尤其是武则天的政策进一步发展完善的。节度使防边格局的形成,表明的是唐廷与周边民族和部族势力关系的变动,这也是影响甚至左右唐朝命运的一件大事。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北朝时代,整个国家和社会占据主流的大事,一是胡汉关系,一是士族与庶族的关系。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必须要搞清这些关系,才能做到提纲挈领,重点突出。同样,汉人与非汉人(或胡人)之关系于唐朝前后的变化,也是理解唐朝主旋律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得知,唐朝建国征服、收降其他各支势力的同时,高祖、太宗也不断用兵周边,试图将中原以外地区的各种胡系势力纳入王朝的控制,以达到大一统的格局。既然将周边胡系势力纳入,就意味着唐朝的统治出现了胡汉内外兼具的二重或多重局面。这是魏晋以来胡人势力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导致胡汉分合关系的必然结果。隋唐两朝若想建立一统化的王朝国家,就必须统合这些胡汉势力。所以,两朝经营中原之同时,将触角伸向周边远域,是此前胡汉关系的逻辑延展。经过高祖、太宗、高宗三朝的经营和开拓,将东北至西南周边内陆各地的势力相继纳入,构成了王朝内外二重结构的格局。
但是这个格局(或体系)并不是均衡的,而是在人群、地域上分作内外二重(或多重)形式,即以汉人及其中原为腹心,以非汉人及其周边为外围,内外主辅依次递进,形成了王朝的架构。用唐太宗君臣的话语表述,就是汉人、内地为大树之本根,非汉人、周边则成为枝叶。它鲜明地表达了唐人内外有别的观念。唐朝初期将周边突厥、契丹、党项、吐谷浑等众多势力纳入统辖范围,采取的控制方法和手段也是内外有别,内地称作“正州正县”与国家的“编户齐民”,它们是王朝的主要依托;外围地区则采取羁縻府州的方式安置胡人,外加都护府予以控制。这种办法可谓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唐廷以府兵驻守的方式控制全国上下,其中多数居守两京内外,形成“内重外轻”之格局。这是前期通行的做法。
然而,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并挺向其东北吞并吐谷浑,直接威胁了唐都西部的纵深之地,随之又展开与唐廷争夺西域腹地安西四镇的较量;北面的突厥降户持续叛乱,复国于草原,并紧随其后南下滋扰;加之契丹、奚“两番”首鼠两端,反复无常。周边的这些震荡,使唐朝前期那种“守内虚外”的格局遭受了空前的挑战,府兵驻防机制逐渐失灵。唐廷遣派都护和边防兵前后征讨,调派数万人的行军反复施压,然而叛乱或造反的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致使朝廷措手不及,终于打算通过调整步伐和变革军事制度以加强防守能力。
节度使体制随之形成,唐廷遣派人员驻守特定地区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防守。为了提高效率,朝廷原有的直接任命将领的权力便给了节度使,让他们掌管所在地区的军事、民政和财政,也就是集全部大权于一身。这样,以特定地区为核心形成的新型权力格局就此展开。
安禄山之所以有能力调动三镇兵马转而对抗朝廷,就是这个机制赋予他节度使这个职位的权力导致的。我们清楚地看到,朝廷将自身的一部分军权转授给军队将领,目的是让他们防守边地,保卫中原核心腹地的安全,但授予的同时并没有形成对这些将领的控制机制,一旦将领统辖自身所属的军队滋扰闹事,朝廷就很难应付。军队士兵之所以能听从将领之命令,也正是他们身系并附属于将领之结果。随着这一系列旨在防边的体制性改变,权力也发生了转移。这种情形恐怕是唐廷未能预料到的。
节度使体系之建构,表面上是军队结构的变化,但支配这种转变的因素,还是周边胡系势力及其政权的建设与唐廷之关系的转变。说一千道一万,唐朝与其控制下的非汉系民族或族群势力如何调整彼此的关系、如何维系,或者说是分还是合,这才是军事制度变迁、安禄山叛乱之生发的内层制约要素。
长话短说,就趋势而言,唐朝立国后所面临的诸多任务之一,就是整合魏晋以来的中原、周边的胡汉关系,通过羁縻府州、正州正县的行政建置,都督府、都护府与军镇的布防,以及胡汉官职的配备等措施,将周边的胡系势力纳入王朝国家的结构之内,从而建设巨型王朝并臻于极盛。这是唐朝统治集团的目标,唐也的确构筑了这个局面。然而,周边势力之反复无常,内外兼统所需要的资源之多和能量之大,使唐不足以长久维持这个局面,终以周边势力兴盛或再度崛起而破局。安禄山叛乱正是这一格局及其形势转变的标志。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
安禄山叛乱对局势产生的长远影响:前后有别。
安禄山叛乱产生的影响,就唐朝而言,打破了朝廷整体性建构的布局,突出表现在长安朝廷对全国控制能力的陡然下降,尤集中在河朔藩镇的割据行为上。这虽是大家熟知的内容,但也是最本质的。与前期统一的架构相对照,后期中央控制力的下降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和后果。
首先是区域地位的分明与逐步实态化。前面我们曾讨论唐朝建国的基本步骤,即以关中为核心宰制山东,面向江南,进而构成王朝的整体布局。这本身就建立在区域化的基础上。一旦建立一统化的王朝,无论在哪方面,都要消除非均衡的状态,达到全国的上下统一。当朝廷的能力增强之时,区域化现象的削弱就愈加明显;反过来,当朝廷的控制减弱,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区域化的再现和区域自身的壮大。唐后期,区域化的主要表现就是节度使控制的地区逐渐增加,自身的独立倾向随之加强,这在河朔、中原等地都有突出的展现。黄巢率军造反,对唐廷的冲击前所未有,各地节镇势力进一步坐大。到了晚唐时期,连长安周边的节镇都纷纷拥兵自重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把朝廷和皇帝放在眼里,朝廷的权威丧失殆尽,一统化格局的景象不复存在。朝廷的合法性完全丧失了。
其次,唐后期,节度使遍布内外各处,他们都在巩固自身、蜗踞地盘以自保,与朝廷的关系若即若离,有的甚至公开叫板和对抗。外围边地则是各胡系部族势力与所在地区的节度使力量结合,或是这些边族首领充任节度使强化自己,于是逐渐形成了盘踞特定地区的胡汉联合势力。譬如契丹固守东北,党项于都城长安北部崛起自立,南诏据守云贵高原,回鹘西迁建立若干政权,沙陀蜗居代北强化自身并形成北方的强盛势力,等等。这些胡人武装崛起和壮大,正是朝廷控制力的下降为他们的兴起提供了机缘。我们前面说过,唐朝建国本身就是融合胡汉势力并整合魏晋以来多民族、多部族势力进而统合为一的,然而,随着唐朝建国后形势的发展变化,胡汉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那些旧有的胡汉差异消解的同时,新型的胡汉关系又萌生了。
原本活跃在天山北麓的沙陀人就是再生势力的典型。他们因为忍受不了吐蕃的控制,便举族内迁,虽然在吐蕃军队的追击下损失惨重,但最终逃到了唐朝控制的地区,从长安北部的灵州转往代北,于唐末形势的复杂激荡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之路,以雄踞代北并参与王朝和地方的角逐而发展壮大。在唐朝被节度使朱温推翻之时,他们与各地节镇将领趁机独立建国,出现了大小王朝、政权各立的新局面。
这表明,在秦始皇建立中原一统化王朝之后,随着东汉的解体,汉系以外的其他民族势力向中原挺进参与王朝建构的新时代从此开始了。隋唐大一统成功之原因,就在于它们吸收和利用了胡汉的各种势力,将中原汉地农耕型的王朝扩展至包括草原游牧地区在内的南北兼具的二重组合的格局,成为复合型的国家。唐朝后期社会分化的事实告诉我们,这种复合型王朝的成形是一回事,如何维系并巩固则是另一回事。
唐朝创立了这种类型的王朝,但它没有能力维系,重新整合再建一统化异质性(复合型)巨型王朝之使命,落在了蒙古贵族和满族贵族的肩上,元和清就是两个较唐朝更成功的典型。尤其是清朝,它不仅是尝试,也是古典时期以来这类王朝的归结和综合,并将其整合到新的层次。也就是在这时,西方势力东渐进入,并以民族国家的观念冲击中国,传统王朝的脚步戛然而止,中国随之步入民族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