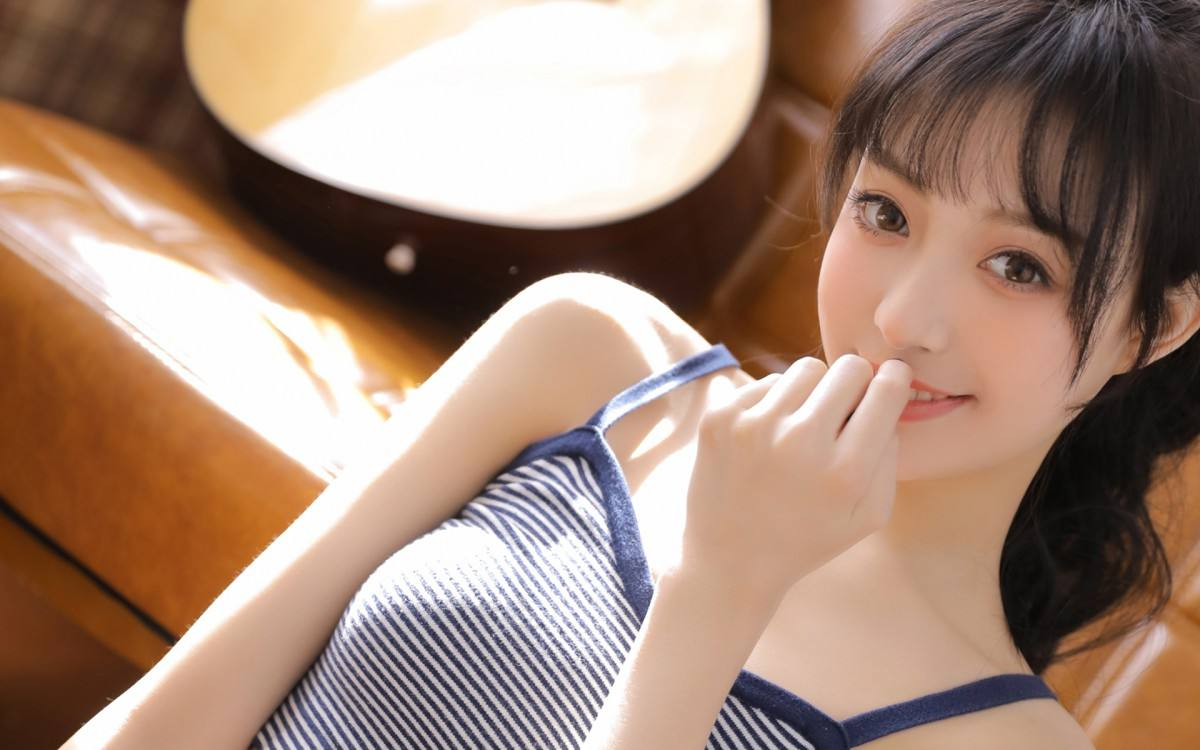梵高是谁_梵高悲催的一生
1853年3月30日,文森特·梵高出生于荷兰一个偏僻小镇,他的父亲是个穷困潦倒的牧师,母亲是个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三十岁依然待字闺中,没办法只好下嫁。母亲懂得绘画和文学,家里每天晚上必备节目,便是一起围着火炉读书。她非常注重吃饭的规矩,她认为,规律、适度的饮食对于塑造健康的体格和健全的道德感至关重要。
梵高从小便显示出过人的艺术天赋。他喜欢读书,阅读速度飞快。他会挑选一个喜爱的作家,然后花上一周一口气读完他的全部作品。他非常喜欢安徒生的作品,我们从他后来很多异想天开的画作中能够清晰地找寻到安徒生的影子:饱含灵性的植物、人格化的抽象、放大了的情绪和唐突的意象。他认为安徒生的童话“万般真实,美妙至极。”
梵高家虽然贫穷,但是母亲坚决不许孩子们跟“下流社会”的人来往。她认为,与出生良好的人为伍,幸福与成功源源不断;一旦交友不慎,失败与罪恶便会紧随其后。尤其劳工和农民,他们灰头土脸,无名无姓,无地无产,不但愚昧低俗到无可救药,更缺少“一颗丰盛的心”(指敏感度与想象力)。“他们不过只有小学文化,为赚得土豆糊口终日精疲力竭。他们的心与他们的头脑一样贫瘠,全然丧失了爱与忧伤的能力。”
但是小镇的上流圈子也看不起梵高一家,梵高一家便成了鲁迅先生写的“站着喝酒穿长衫唯一的人”,只能待在家里,好像被隔绝在一座孤岛上,唯有彼此相伴。
梵高从小是个“怪男孩”,忧郁多疑,性情躁动,不擅交际,虽然爱开玩笑,但是一点都不好笑。他经常感到孤单无助,忧心忡忡。唯一能给他带来快乐的,就是写字。早在识字之前,他就习惯了在纸上涂涂画画。母亲每天带他出去写生,梵高的绘画生涯由此开始。但他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自己的每张习作都不满意,一旦有了挫折感,就会自暴自弃,故意跟身边人找茬,像公鸡一样好斗,是“家里最不好对付的小孩”。
为了逃避家里的琐碎和压抑,他经常独自一人来到郊外的田野上,眺望一望无垠的黑麦和玉米垛。他穿过高高的麦田,沿途“不折断一根茎秆”。他在学校里也没有朋友,在同学们眼里,他“很孤僻”、“是个异类”、“与其他孩子从来没有交集”。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会离开镇子在外游荡几个小时。”
孤独定义了梵高的童年,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段阴郁荒芜的岁月”。
16岁,梵高进入膝下无子的伯父的画廊公司,成为伯父的“门徒”,准备日后继承伯父不菲的资产。作为学徒,梵高每天干的便是给画框除尘、摆放橱窗之类的杂活。梵高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并且对艺术产生了狂热的兴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地艺术家、艺术史和艺术收藏的书籍,经常去参观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他给弟弟写信说:“多看些古董画是件好事”。
1871年,18岁的梵高认识了19岁的白富美卡罗琳,卡罗琳住在“令人艳羡的大别墅里。”卡罗琳性格外向、大大咧咧、无忧无虑,与内向古板的梵高性格截然不同。但是梵高对这位女神只能“美人如花隔云端”,可望而不可即。因为卡罗琳已经和表哥订婚了,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炫耀手上的钻石大戒指。
1873年,梵高来到伦敦,管理画廊的库房。库房里没有一张好画,他感到无聊,孤独,寂寞。为了不再消沉下去,他与已婚的卡罗琳开始了亲密的通信。他在信中写道:“你俘获了我的心,如此真切……你的面容在我心上挥之不去。”但是卡罗琳严厉地斥责了他的痴心妄想。受伤的梵高放下画笔,孤独地舔舐着伤口。他不思饮食,蓬头垢面,远离人群,无心工作,遭到伯父的严厉批评。伦敦没有旷野,他只能在下班后“久久流连于那些后街小巷中”。
1875年初冬,一群标新立异的青年画家荒谬地宣称,他们使用的亮色和松散的笔法能以更科学的方式捕捉形象,“即使最精明的物理学家也难以找出纰漏”。他们以“无名者”自居,但被传统画家给予了“印象派”和“疯子”的称谓。他们认为印象派的作品是“一摊烂泥”,是“猴子摆弄一堆颜料”的结果,“惨不忍睹”。
梵高最初对这帮印象派画家毫无兴趣,“完全没有留意到他们的存在”。他埋头沉浸诗集、大部头哲学书、自然手册、奋斗史、畅销小说和俗套的情爱故事,他还涉猎枯燥的历史书,尤其喜欢阅读人物传记。他经常叼着烟斗徜徉在巴黎街头,避开一个又一个博物馆,却在坟墓前久久驻足。
吊儿郎当的工作态度导致他很快被画廊解雇。他把被炒鱿鱼诗意地比作了一个“微风一吹就会从树上掉落的成熟苹果”。家里对他彻底失望,父亲责备他毫无上进心,抱有“病态的人生观”,无能到“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失业后,梵高行走在英伦大地上,从一地辗转到另一地,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不论天气,不论时间,在荒野歇息,在田地间觅食,在小旅店填饱肚皮,或者什么也不吃。他衣衫褴褛,皮肤灼裂。
他找到一份书店售货员的工作,可他完全无法胜任这份工作。他要在桌前从早上8点站到午夜(其间有两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在老板眼里,他大多数时候都在“混时间”,也无法取悦客人,只能卖信纸和向孩子们卖半个铜板一张的画片。“几乎一无是处”,“他对图书交易一无所知,他也完全不想学。”
同事们非常排斥他。梵高坚持戴一顶破旧的礼帽,“任何人看到它,都会有把那帽檐撕扯下来的冲动。”室友们讥讽他太一本正经,故意制造噪音打搅他读书。他们叫他“怪人”、“奇怪的家伙”和“神经病”。
严重的挫败感和孤独感让梵高第一次崩溃了。他开始酗酒,头痛越来越严重。“当你有很多事想要做时,”他抱怨,“你有时会变得很迷茫:‘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我又要去向哪里?’大脑也开始眩晕。”他用红粉笔在蓝色厚纸板上创作了一幅画,挂在一所学校的地下教室里。即使在白天也需要点上煤气灯才看得见这幅作品。“我兴许应该不时地尝试一下创作,”他说,“没准我还能成功……即使没成功,我也可以留下些印记。”
他决定用绘画来驱散孤独,并且成就自己。他极其专注地蹲在一张折凳上,猫着腰,驼着背,把素描簿架在膝盖上,一直画到熄灯为止——如果天气允许,他会在外边的花园中画。仅仅两周时间,他就完成了120幅作品。“我的手和脑都变得越来越灵活强大”,他说,虽然这些练习“十分苛刻”, “极其枯燥”,但却不敢松懈,因为“一旦停下来,我就会迷失,”“我认为,不论怎样,我必须前进,前进。”
为了从自然中获取创作灵感,他每天在镇子里徘徊,描了不少肖像:扛了一麻袋煤的女人、收获了土豆的一家子、吃草的奶牛。他把折凳搬到大街上,像涂鸦的孩童一般草草记录下所见所闻——作画的技巧完全没受过任何训练,连他自己都认为“很拙劣”。他饱含热情和希望地一遍又一遍描绘同一个场景。“我已经画过五次播种者,”他说,“但我还会再画,我对播种者的形象实在太着迷了。”
由于没有收入来源,他的生活只好单纯依赖弟弟接济。这种接济从最初迫不得已的请求,发展成后来索要更多资助的恶性循环。“老实说,要好好画画,我每月至少需要100法郎,”他略带警告意味地对弟弟说:“贫穷会让最聪明的大脑失灵。”“虽然我已失意落魄”,“但你光耀了门楣”。他充满歉意地祈求弟弟对自己保持耐心,并感伤地允诺将来一定会报答弟弟。“终有一天,我的画能卖上几个铜板。”
梵高投身绘画的唯一初衷就是赚钱。此时他已经28岁,换了很多工作,可是过分孤僻和不善交际的性格让他处处碰壁,无论在哪儿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因此他想到了搞艺术。搞艺术是个孤独的职业,需要的唯一条件恰恰是埋头创作,闭门不出。有鉴于此,家里人对他也很支持,寄来了必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也兴致勃勃地写道:“我要尽快学会创作一些像样的、能够卖出去的画作,这样我就可以从工作中直接得到些许酬劳。”他不断地向父母保证:“以绘画为生,我绝对没有问题……好的插画师现在轻而易举就能够找到工作……这样的人现在供不应求,这些职位的报酬也都很可观。”
但是众所周知,搞艺术是个烧钱的行当。家里人很快便供不起他的花销,要求他自己也找一份工作。迫不得已,梵高找到一份为一位铁匠画炉子的工作。
期间梵高爱上一位姑娘,可是姑娘不爱他。梵高上门求婚,姑娘的父母和兄弟告诫他,除非他的财务前景有所改善,“否则没有丝毫机会赢得她”。梵高见不到姑娘,怒了,将手放在煤气灯的火焰上,要求道:“我只要求见她一面,只需要我能忍受我的手被这火焰灼烧这么长的时间。”即便如此,姑娘还是没见他,姑娘的哥哥上前灭掉了灯。
梵高穷困潦倒,欠下很多债。债主们堵在家门口,他告诉债主,只要一收到钱,就会马上付钱,但现在确实身无分文。梵高恳求债主离开家,债主抓住他的脖子,将他推到墙边,把他直挺挺扔在地上。他不断诉说自己的贫困,并且迅速地确认了弟弟对所有作品的所有权(这样债主们就无法拿走这些作品),考虑溜之大吉。
30岁,梵高回到家乡,认识了隔壁的大龄剩女玛格特。玛格特43岁,姐妹三人,都没有出嫁,她最小。她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小镇里,没有出过远门,相貌普通,孤芳自赏,心地善良,富于钱财。她对谜一样的梵高产生了好奇心,经常一大早便站在窗前,看着梵高背着马扎画架颜料,佝偻着身子,走到田野上写生。傍晚时分,她来到梵高家里,约他一起散步,斜阳晚照,格外美好。
梵高产生了和玛格特结婚的想法,因为玛格特可以给他金钱上的帮助,而这正是他最为缺乏的。但是同所有家中略有钱财怕人觊觎的家庭一样,两人的爱情遭到女方家人的坚决反对,玛格特为了反抗家庭的阻挠,不惜服毒自杀,幸亏被梵高送往医院救活。即使如此,玛格特家人依然把她送到远方亲戚家里,以免玷污家族名声。她们宁愿女儿孤老终生,也不愿女儿嫁给一个不名一文自称画家的怪物。梵高去女方家大吵大闹,然而无济于事。两人就这么被棒打了鸳鸯。
此时梵高的绘画技巧渐入佳境。事实证明,即使一个天才画家,也要经过不断尝试和练习,才能把身上的“天赋”激发出来。如果说天赋是一块玉,那么反复练习就是一个切磋琢磨的过程。只有靠日积月累的机械重复将外面坚硬的顽石取掉,才能看到美玉闪闪生辉。
一个男孩曾经回忆梵高在画室工作的场景:(他)穿着长长的羊毛内衣,戴着稻草帽,拼命地抽着烟斗: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景象。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和画架之间有一些距离,双手交错在胸前,久久地盯着画。突然他会跳起来,好像要攻击画布一样,在画上快速地画几笔。然后又慌乱地退回到椅子上,眯着眼睛,擦拭着额头,搓着手……村子里的人都说他疯了。
另一个男孩回想起梵高在田野里寻找地方放画架的情景:他站在这儿,又站到那儿,又换到更远的地方,再回到这里,然后又站到前面,直到人们说,那个傻子又站到那里了。
由于常年跟农民打交道,以农民和田野为创作题材,梵高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农民,“我在画布上作画,和劳动者在土地上耕作并无二致。”对一幅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他反复强调,这是一幅“由一位会画画的农民创作”的。他用一个冬天的时间,三易其稿,画了一幅《吃土豆的人》,内容是农民一家四口在昏暗的灯光下围在桌前吃土豆。桌上还有一个人,就是他。
但他这种“自甘堕落”的行为惹怒了家里所有人,一向以“有身份的人”自居的母亲大发雷霆,和妹妹一起将他赶出了家门。
1885年初秋,黄叶飘零,梵高在一家颜料店举行了自己首次公开画展,可以想象,问津者寥寥无几。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还找了一份为餐馆画一些装饰画或招牌(例如替鱼贩画鱼的静物画)的“兼职工作”。“让大家看到我的作品,是我的心愿。”他添置了新衣服,开始有规律地吃饭,和别人讨论新的成功秘诀。“不能看上去总像是没吃饱饭似的,或是太寒酸,”他说,“相反,必须设法穿戴得体面一些才行。”
1887年,34岁的梵高爱上了45岁的咖啡店老板塞加托丽。他之所以爱上这个大十几岁的女人,目的只有一个,便是希望这个女人可以资助他一些钱,让他把绘画事业继续下去。此时的梵高,已经不相信爱情。他悲愤地说:“当我应该恋爱的时候,我却将青春奉献给了艺术,觉得艺术比爱情要神圣。”他怀疑“恋爱中的人是否比那些将心灵奉献给艺术的人更神圣”。
但是软饭显而易见没有那么好吃。塞加托丽明确拒绝了他的求爱,并且让他滚,还让一个咖啡馆服务员上门警告他。梵高不为所动,塞加托丽找了一帮混混,对他大打出手,不仅朝他脸上砸啤酒瓶,划破了他的脸颊,还将他的一幅花卉画扔到他头上。梵高脸上淌着血,羞愤难当,绝望透顶。
同所有单身狗一样,梵高爱上了喝酒:下午喝苦艾酒,晚餐喝红酒,在夜总会自由地喝啤酒。他个人偏爱法国白兰地,随时都喝。他需要这种甜蜜的“麻醉”来治疗愈来愈烈的抑郁症,还辩解说喝酒可以“加快血液循环”,以抵御严冬的寒冷。他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多多享受你自己,要比不懂得享受来得好,”他劝告妹妹惠尔说,“对艺术或爱情不要太当真”。
1888年圣诞节,弟弟的结婚和挚友高更的离去终于让他崩溃了。一直以来,弟弟都是他的经济支柱,高更是他多年绘画生涯中唯一的知音,换言之,这两个人是“希望”的代名词。可是,就在这个圣诞之夜,希望离他而去,他彻底绝望了。他站在镜子前,拿起剃刀,抓住自己一只耳朵,猛地一划,便划下半拉。他用报纸包了划下的半只耳朵,送给曾与高更经常交往的一个女孩。
两个月后,他的精神出现了错乱。他晚上经常梦魇,眼前出现幻觉,在街上大喊大叫,胡言乱语,跟踪陌生人到他们家里。“我时而满腹热情,时而歇斯底里,时而又觉得自己能预知未来,这些时刻交替上演,让我十分痛苦扭曲。”他说。他很少吃东西,经常酗酒,昔日的美好时光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殆尽。他产生了近乎偏执的臆想:有人试图毒死他。
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医生认为他的病症是“一种癫痫”。不是自古以来为我们所熟知的、使羊羔抽搐以及使身体瘫倒的那种癫痫,而是一种精神癫痫——大脑运转的突然失灵:大脑中的思想、感知、推理及情感上的突发性崩溃,并由此引发奇怪而夸张的行为。医学上称其为“潜伏性癫痫”,这种疾病每次发作会间隔很长的潜伏期,其间病人过着相对正常的生活,并没有意识到梦魇正在脑中形成。由于发作原因不明且病症形式多样,还被称为“隐蔽性癫痫”。
听了医生的诊断,梵高痛诉家史:他的外祖父“死于精神疾病”,姨妈终身未婚,一生深居简出,饱受癫痫困扰。一位舅舅自杀而亡,一位伯伯在35岁时,也就是梵高现在的年纪遭遇了第一次“癫痫发作”,英年早逝。另一位伯伯也在40岁时经历了不明疾病的“发作”。一位堂兄“遭受了某种严重的癫痫性发作”,进了精神病院,最终自杀身亡。医生在他的住院记录中总结道:“这位病人所遭受的仅仅是其家人曾遭受的痛苦的延续。”
医院于是给梵高安排了一个很大的房间供他作画。就是在此地,就是在此时,梵高的绘画理念终于成熟。他用鲜艳的色彩和魔幻的笔法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其中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和想象。他用“直觉和感受”勾画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普通人眼中所见的事物,这些事物只存在于他的脑海中。
1889年盛夏时节,梵高病愈出院。他体格强健,肩膀宽阔,脸色健康,面带微笑,非常结实。他每天背着作画的工具去田野里作画,画的最多的便是麦田,金黄的,一望无垠的,只存在于自己想象中的麦田。一天晚上,他回到了家,肚子上有一个弹孔。他跟别人说,自己偷了邻居的手枪,朝自己肚子里开了一枪。但是医生和警察没有找到手枪,也没有找到他的绘画工具,而且推断出,开枪的位置离他应该有一段距离。几十年后,有健在的目击者站出来说,一些“年轻的男孩”在玩耍时意外地打中了梵高。因为害怕被控谋杀,这些男孩从来没有主动站出来过;而善良的梵高选择了保护他们,没有说出真相。
1889年7月29日午夜时分,梵高在弟弟的怀抱中停止了呼吸,临终留下最后一句话:“我想就这样死去”。
梵高去世不久,他的弟弟也得了精神病,并于一年之后去世。其余两个弟弟妹妹也先后得了精神病,弟弟自杀,妹妹在精神病院住了四十多年,多次自杀未遂。
梵高去世四十年后,“印象派”创作手法在文艺界大盛,梵高声名鹊起,如日中天,他的《向日葵》和《麦田》等画作被推上神坛。他落魄时曾经请隔壁木匠制作一张桌子,并且画了一张草图。木匠的儿子找到这张草图卖掉,衣食无忧地活了下半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