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何不放过张廷玉_乾隆不肯放过张廷玉的原因
一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不过其当政之初却是手忙脚乱,因为雍正的驾崩过于突然令其接班极为仓促,年仅二十五岁的他几乎没有政治经验,也完全没有做好当皇帝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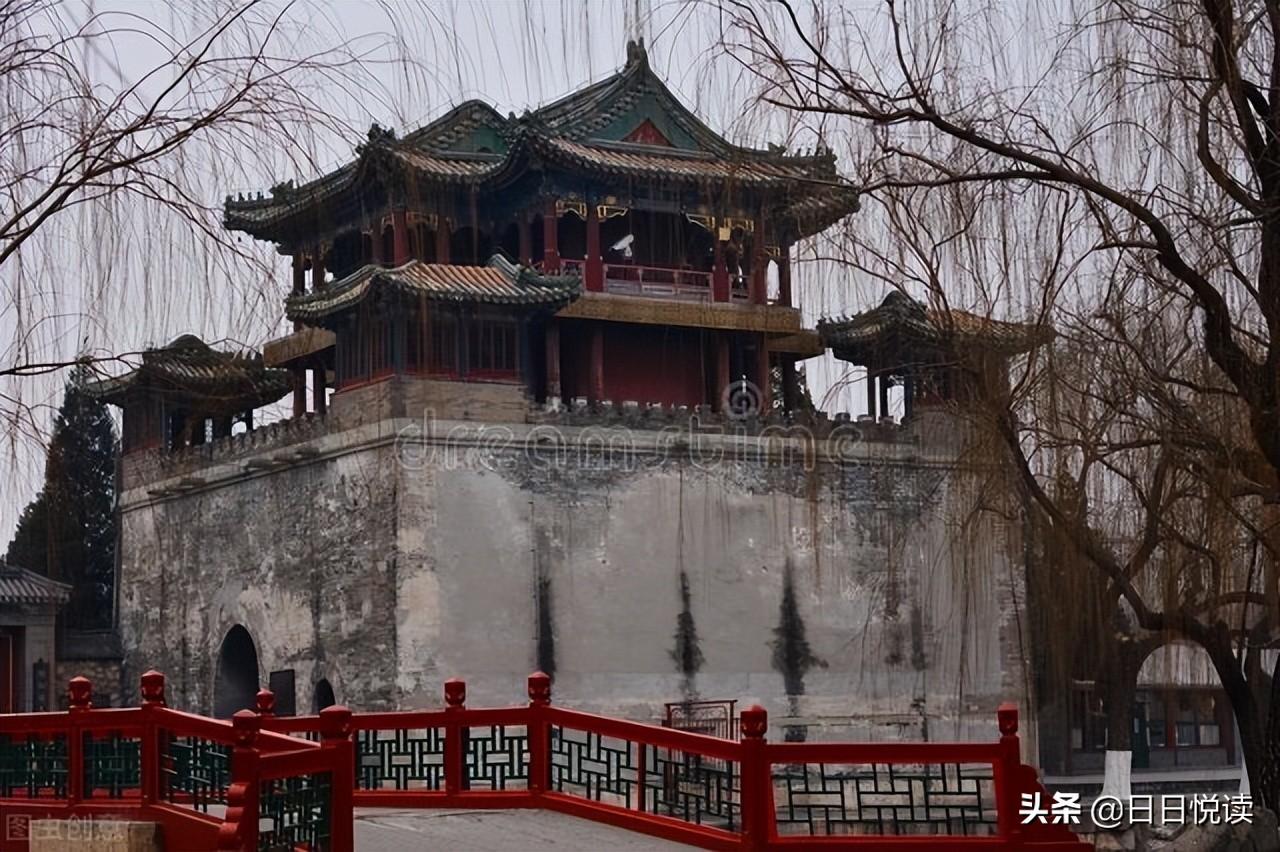
不过,好在雍正给他留下了鄂尔泰、张廷玉两大重臣,在后者的帮助下,乾隆才得以顺利接管朝政并及时的稳住阵脚。
张、鄂二人为官数十年,以其对各级官僚体系及朝政运作的熟稔程度,对乾隆初政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让乾隆感到不满的是,随着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地位的不断上升,其身边也日益形成利益小集团。以鄂尔泰为例,其子侄辈多半为总督巡抚,如鄂容安为两江总督,鄂弻为四川总督,鄂宁为云贵总督,鄂昌为甘肃巡抚,鄂乐舜为山东巡抚,可谓满门显贵,家族势力也大为膨胀。
张廷玉的情况也比较类似,其家族子弟多为达官要职,如其弟张廷璐曾任礼部侍郎,其从子张若溎曾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吏等,长子张若霭官至礼部尚书,次子张若澄为内阁学士等。此外,桐城张、姚两姓为当地大族并世代联姻,时称“天下缙绅,张、姚二家占尽其二。”
鄂尔泰、张廷玉是雍正遗诏中指名要配享太庙的重臣,其在位日久,位高权重,即便二人并无植党企图,但其身边总少不了趋炎附势之人。大臣们各怀揣度攀附之意,由此分出派系,彼此争权夺利。
大体而言,鄂尔泰一派主要以满人督抚为主,另有尹继善、史贻直等朝中大僚;而张廷玉的支持者多为科举出身的汉人官僚,其中不乏朝中九卿及地方督抚。颇具讽刺的是,雍正生前最恨朋党,而其最信任的两位大臣在乾隆朝后竟然成了两大朋党之首领。倘若雍正地下有知,或许也只有尴尬苦笑了。
对于鄂、张两党,乾隆也是心知肚明,其采取的策略是“擒贼先擒王”,矛头直指其首领。首先被打击的是鄂尔泰,其部分原因是鄂尔泰为人傲慢,行事张扬,加上结党营私的吃相外露,因而被乾隆多次降旨“严行申饬”。乾隆六年(1741年),御史仲永檀参奏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善,鄂尔泰及其长子鄂容安相继被卷入,乾隆甚至放出如此狠话,“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独不能重治你的罪么?”战战兢兢数年后,鄂尔泰于乾隆十年(1745年)病逝,总算是福大命大,不但保全了名节,而且还顺利地配享了太庙。

二
相比而言,张廷玉就要老道圆滑多了。如时人所说,“张文和(即张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画喏坐啸,目击狐鼠之横行,而噤不一语。”张廷玉也不去管它,笑骂任他笑骂,他只想当个太平宰相,正如他的那句名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安静静地致仕荣归,这辈子也就算功德圆满,再无他求。对此,乾隆也觉得有些过分,说“张廷玉善自谨而近于懦者!”
张廷玉的这种状态,说好听一点叫稳重平和,说难听点就是不思进取,这让雄心炽烈、急于表现的乾隆当然感到不满。这时,鄂尔泰的去世倒是个好时机,乾隆乘机调整中枢,三十出头的青年权贵讷亲被任用为军机大臣,而且位列于张廷玉之前,这让后者心中多少有些尴尬而不自在。
一年后,乾隆又下谕旨,称“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赴阙,未免过劳,朕心轸念。嗣后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换言之,张廷玉已经被排除在核心圈外,其地位的急剧下降已成事实。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岁月不饶人,自然规律不能抗拒。乾隆三年(1738年)后,张廷玉自感精力大不如前,看文件眼花,写字打颤,正如他在请辞兼摄吏部的奏折中说的,“今犬马之齿六十有七,自觉精神思虑迥不如前,事多遗忘,食眠渐少。”不过这次却被在位未久的乾隆给驳回了。
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廷玉最看重的长子张若霭突然病故,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张廷玉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此后,张廷玉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如《啸亭杂录》中说的一个笑话:张文和公晚年颇以谦抑自晦,每遇启事者至,动云:“好、好。”一日,有阁中胥吏请假,公问何事,曰:“适闻父讣信。”公习为常,亦云:“好、好。”舍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觉也。
乾隆九年(1744年),张廷璐告老还乡时,张廷玉作诗送别。在诗中,张廷玉对老弟的退休归里颇感羡慕,而对自己能否顺利引退则似无把握。诗末两句,张廷玉希望自己返回故里时,老弟能在家门口“拄杖花前一笑迎”,兄弟俩把酒话旧,共度余年。不过,这只是他的美好愿望,因为张廷璐在回乡次年即因病去世,而张廷玉的引退问题则屡经波折,几成噩梦。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趁着入宫赴宴的机会向乾隆提出致仕的请求,说自己“年近八旬,请得荣归故里”。说到动情处,其“情辞恳款,至于泪下。”张廷玉本以为,自己主动让出位置,乾隆会心领意会,顺势推舟,以便安排新人上岗。但他没想到的是,乾隆仍拒绝了其请求,说“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
张廷玉听后争辩说,宋、明两朝也有配享大臣乞休回家的,如明太祖时期的刘基等。更何况,七十悬车乃古之通义,老子曾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而引退,于国于臣都是好事。
张廷玉的话让乾隆听了很不痛快。要知道,刘基求归是朱元璋猜忌功臣的结果,张廷玉以此为例,岂不是把自己也当成了朱元璋那样的刻薄寡恩之主?作为朝中重臣,一身任天下之重,岂能以艰钜自诿,而以承平自逸?如果七十必令悬车,又何来八十杖朝之典?如必以泉石倘徉,高蹈为适,独不闻武侯鞠躬尽瘁之训耶?
话说到这里,张廷玉也不敢再辩了,只得免冠叩首,呜咽不能自胜。眼看老臣流涕,乾隆也不好怎么样,当日之辩无果而终。退朝后,一向争强好胜的乾隆觉得道理没有说清,于是又在次日发布长篇谕旨,将这番争论公布于天下。
谕旨中,乾隆一下就把此事提到了“君臣大义”的高度,说“为君则乾乾不息,为臣则蹇蹇匪躬,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张廷玉身为老臣,“不独受皇祖、皇考至优至渥之恩,不可言去。即以朕十余年眷待之隆,亦不当言去。即令果必当去,朕且不忍令卿遽去,而卿顾能辞朕去耶?”
乾隆又说,如果有人参奏张廷玉恋栈要职而求去,这尚可理解;无人参奏而自行求去,则有违君臣大义。为人臣者,断不可存此心;如预存此心,必将漠视一切,君臣间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视矣!如此,年至则奉身以退,谁又肯为国尽心出力?“此所系于国体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更何况,“我朝待大臣恩礼笃至,而不忍轻令解职。大臣苟非隆老有疾,不轻陈请,恐不知者反议其贪位恋职,而谓国家不能优老。”
最后,乾隆还是对此事做了一定的妥协,令张廷玉不必兼理吏部的所有具体事务,改由大学士来保兼管吏部事。
高阳在《柏台故事》中说,乾隆之所以不准张廷玉退休,原因有二:一是担心张廷玉回到桐城故里后,以其肚子里的存货,如雍正继位及弑兄屠弟,杀年羹尧、隆科多灭口等秘事恐怕会流传民间;二是乾隆认为张廷玉虽然祖籍桐城,但其家数代为官,自小“长于京邸,子孙绕膝,原不必以林泉为乐”,在京城同样可以“从容及仗,颐养天和”。
高阳之说也不是全无道理,不过其所说的秘事未必是真,而以张廷玉的谨慎性格,所谓秘史外传也没有得到事实的证明。如以乾隆的个人角度来看,张廷玉很可能是因为他在朝中受了冷落、心生不满所致。而且,张廷玉一再乞休的做法明显表明,他对自己的忠诚和个人感情远不及对父皇雍正,这才是让乾隆感到十分生气的原因所在。

三
此时的张廷玉,运气也有点背。在乞休被拒不久,因为孝贤皇后的突然去世,乾隆性情大变,大清官场人人自危,张廷玉也不能例外。当年九月,乾隆《御制诗集》刻本刊行后,由于其中讹误甚多,作为总裁官的张廷玉被交部议处;十月,翰林院所撰的孝贤皇后冬至祭文中用“泉台”一词不妥,张廷玉作为撰文人之一,也被罚俸一年;十一月,张廷玉等又因拟写票签错误而被交部议处,最后被销去二级。
拟旨、文字原本是张廷玉的优长,但乾隆偏要在这个问题上一再挑刺,这让张廷玉难免有“伴君如伴虎”之惧。张廷玉做了一辈子的官,一直以来都是顺风顺水,基本没犯过什么错,但要是事到终了而晚节不保,那前面做得再好也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想到这里,张廷玉渴望退隐的念头也就越来越强烈,及时抽身退步,给自己的一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就成为他余生最大的愿望了。
乾隆十三年的风波日渐退去后,张廷玉终于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在次年十一月的一次君臣谈话中,乾隆发现张廷玉这一年多来的变化太大了,其思维明显迟滞,说话也时常颠三倒四,昔日警敏周密之能臣,已成老态龙钟之颓势。有见于此,乾隆心中也不免感叹,岁月无情,概莫能外!
召对结束后,乾隆顺便问起其身体状况,张廷玉趁机详陈衰疲之状,并试探性地提出退休请求。这次,乾隆总算动了恻隐之心。数日后,乾隆发布谕旨,称张廷玉“自今年秋冬以来,精采矍铄,视前大减,……夫座右鼎彝古器,尚欲久陈几席,何况庙堂元老,谊切股肱。然亲见其老态日增,强留转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之后,乾隆命人将谕旨送到张府,让张廷玉自择去留。
按乾隆的设想,老练过人的张廷玉应该明白自己的意思,回奏时应一面陈述自己老病不堪,难于支持,另一方面又犬马恋主,不忍离去;这样的话,乾隆才好顺水推舟,做出关心老臣的姿态,特命其荣归故里,优游泉林。如此,君臣应对才算是干净漂亮,成就一段佳话。
但是,让乾隆大失所望的是,张廷玉见旨后喜出望外,当即上奏谢恩,“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事已如此,乾隆也看出张廷玉一来是求去心切,二来也确实是老了,已不复当年的精明。既然这样,就放他走吧!
为此,乾隆再发谕旨,说“大学士既陈奏恳款如此,应加恩遂其初愿,示朕优老眷旧,恩礼始终之意。著准以原官致仕。”此外,“伯爵非职任官可比,仍著带于本身。”因为此时正是严冬,乾隆又安排张廷玉在明年春天启行,届期另颁恩谕,南巡时也可相见。谕旨最末,乾隆还展开联想的翅膀,说十年之后,“朕五十正寿,大学士亦将九十,轻舟北来,扶鸠入觐”;届时,君臣重逢话旧,“成堂廉盛事,不亦休欤!”
按说,张廷玉的一生仕业到此算是划上圆满的句号了。但鬼使神差的是,张廷玉这时又想起了“配享”问题,这问题不解决,他走也走得不安心。是啊,此前乾隆在谕旨中说过,“从祀元臣,岂有归田终老之理”,而自己的对头、文渊阁大学士史贻直等人也曾参奏自己不当配享,这万一回到故里而失去配享荣誉,未免有些太过可惜了。
辗转数日后,张廷玉在儿子的搀扶下进宫面见皇帝,请求以一言为券,保证自己死后能配享太庙。如此惊人之举,若是换到以前,张廷玉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
乾隆听了张廷玉的哀哀请求后也是惊诧莫名,继而十分不快。他万万没想到,张廷玉竟然会得寸进尺,所言所行迹近要挟,竟然要皇帝写保证书!且别说自己没不让张廷玉配享太庙的打算,就算有,那也容不得张廷玉指手画脚啊?张廷玉这么想、这么干,明摆着就是信不过他嘛!
想到这里,乾隆真是差点把肚皮气爆。但到最后,他还是忍住了这口气,算了,好事做到底,不跟这老糊涂计较了。毕竟,张廷玉是三朝老臣,雍正遗诏“保其始终不渝”并令其配享太庙,就算不看张廷玉的面子,也要顾及父皇的面子吧。
当然,身为皇帝之尊,保证书是不能写的,不过可以破例再开一次恩,以诗为券,算是答应了张廷玉的请求。当晚,乾隆越琢磨越不是滋味,于是他写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给张廷玉,曰: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乾隆诗中的情绪是明显的,不过得了保证的张廷玉在兴奋之下竟没看出其中的毛病,他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按理,张廷玉在次日应亲自进宫谢恩,但或许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加上天气严寒,第二天他竟未能亲自赴宫而只是命其子张若澄代其前往到宫门谢恩。而正是这一小小的疏忽,结果惹来了漫天的大祸。
四
就像压力锅一样,乾隆对张廷玉的不满并非一日,这次一再加恩、再三容忍,而张廷玉却并不感恩,甚至连基本的礼节都如此轻慢,这下乾隆的愤怒算是到了临界点了。其当即命军机大臣拟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这下,张廷玉知道麻烦大了,他也顾不上严寒和病体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宫中磕头认罪。
但是,乾隆的火气更大了。因为事情太清楚了,令其明白回奏的谕旨还没发到张家,张廷玉却已经知道内情,天还没亮就赶来认罪,这不是明显有人走漏风声,暗通信息吗?军机处一向号称严密,如此以往,这还得了?
于是,乾隆将张廷玉当面痛骂一顿后,当晚又亲自缮写了一篇上谕,大加痛斥。接着,乾隆又开始追究军机处泄露消息的责任。
被责之后,张廷玉回奏称“十三日实因心恐谢恩稽迟,急欲趋阙泥首,是以向早入朝,并未先得信息。”看到这里,一向爱较真的乾隆又不高兴了,说如果十三日“因风寒严劲,步履不前,则次日何尝不寒?且何难于谢恩摺内声明?……是日承旨系傅恒、汪由敦二人,以二人并论,则非汪由敦而谁?”
汪由敦为张廷玉说情固然不假,但乾隆心想这事也可能错怪好人,于是又给自己留下余地,说就算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不是汪由敦送信,那也必定是军机处司员、中书等有人送信。张廷玉在军机处任职二十余年,这些人都是他的属员,暗通消息也在情理之中。此事若严加审讯,不难查个水落石出。不过,朕自即位以来,一再包容张廷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为这事遽兴大狱也大可不必。但有一点必须搞清楚了,朕绝非可以随意朦混了事的人,且张廷玉摺内于汪由敦不涉一字,明系避重就轻,其荐汪由敦,非以爱之而实害之也。如今汪由敦已经被革职留任,张廷玉也自请交部严加议处,那好,就交付廷议,看看大臣们作何公论。
皇帝定了调,大臣们当然心领神会,廷议结果是“张廷玉除不准配享外,应革去大学士职衔并伯爵,不准回籍,留京待罪。”对此,乾隆很是满意,说张廷玉之罪,“固在于不亲至谢恩,而尤在于面请配享”,试问他为何非要朕“一言为券”?明摆着就是信不过朕,这才是朕最生气的地方!试想太庙配享的都是功勋卓越的元老,张廷玉何德何能,有何功绩,可以和那些元勋相提并论?鄂尔泰还算有平定苗疆的功劳,张廷玉所擅长的,不过是谨慎自将,传写谕旨,所谓“两朝纶阁谨无过”罢了!
说到这里,乾隆总算把自己压了多年的真心话说出来了:“在朕平心论之,张廷玉实不当配享,其配享实为过分。而竟不自度量,以此冒昧自请,有是理乎?”
骂也骂了,真心话也说了,感觉舒畅的乾隆又开始扮好人,说张廷玉虽然不配配享,但看在他是耆旧大臣并蒙皇考隆恩异数的份上,这次也不跟他计较了。说到底,配享是先皇所赐,这个朕不能改,但伯爵是朕所赐,张廷玉既对朕毫无感情,那也不必给他,“着削去伯爵,以大学士原衔休致,身后仍准配享太庙。”至此,张廷玉乞休与配享之事算是告一段落。
从此事件也可看出,乾隆对张廷玉的看法与父皇雍正大为不同,而其中也彰显了两人性格的极大差异。平心而论,雍正为人毅定阴鸷,但其性格中却有着天真任性的一面,其施政处事常有冲动急躁之举,而张廷玉办事周密细致,耐性极好,两人恰好互补,因此君臣相得,十分融洽。在雍正看来,张廷玉不仅有才华有能力,而且品德高尚,忠于人主,称之为“纯臣”也不为过。
至于乾隆,情况就不一样了。张廷玉是精明人不假,但乾隆同样是精明人,一样的世故,一样的玲珑多窍。所谓“同类相斥”,乾隆一眼就看出了张廷玉身上的“巧”和“滑”。在其看来,张廷玉表面上勤勉尽责,背后却心机极深,很多事都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只不过手段高明,善于掩饰,世人不知,为其蒙蔽而已。从乞休与配享这事就可以看出,张廷玉“辗转思维,惟知自私自利,不惟得之生前,而且欲得之身后。”
在乾隆看来,张廷玉这是什么行径呢?是典型的巧宦心术,把做官当成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时势有利就全力营求,时势不利就主动求去,以图保荣避祸,哪里算得上纯臣所为?
张廷玉辛辛苦苦一辈子,没想到最后落得灰头土脸,名誉扫地。心惊胆战之余,他只想赶快回乡,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五
转到来年三月,张廷玉按之前“明春回乡”之旨请示乾隆,以备启程。这次,乾隆倒也算给面子,说上年的事情弄得很不愉快,但近来详加体察,张廷玉“实乃龙钟昏愦,力不能支。当时闻命之下,精神短浅,或心思实有不到,而非出于恃恩疏节,亦未可知。”
作为和解,乾隆命“赐给御制诗篇手书二卷,并御用冠服数珠如意诸物”,起程之日,“仍令散秩大臣领侍卫十员往送,用示朕优老眷旧至意。”
张廷玉的运气也着实是背到家了。就在他收拾停当、准备启行之时,皇长子永璜去世了!张廷玉曾为永璜的师傅,这时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只能一次次行礼如仪。好不容易熬过初祭,丧礼告一段落,张廷玉归乡心切,于是又向皇帝上奏,要马上启程。
话说乾隆死了儿子,而且是自己对不住的皇长子,此刻心情简直恶劣透了,浑身像吃了枪药,有气没处发。张廷玉这一上奏,无疑是火上浇油,硬把自己撞在了枪口上。
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借着额驸、超勇襄亲王策凌配享太庙之际,乾隆指桑骂槐地说,“详阅配享诸臣名单,其中如费英东、额亦都诸臣皆佐命元勋,汗马百战,功在旂常,是以侑享大烝,俎豆勿替”。大学士鄂尔泰配享已过优容,张廷玉更是不当配享。彼在皇考时,不过以缮写谕旨为职,自朕御极十五年来,毫无建白,毫无赞勷,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做做样子而已。
说完这段刻薄话后,乾隆旧事重提,说张廷玉因乞休、配享事被革去伯爵后,仍“靦然以老臣自居,并不知感”;其一心求归,不巧遇上皇长子定安亲王之丧,甫过初祭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安亲王师传,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谓尚有人心者乎!?”最后,乾隆令将此旨及配享诸臣名单交于张廷玉,让他自己说说看,到底有没有配享的资格。
话说到这份上,张廷玉只得自打耳光,说自己“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复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身后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当增愧。……敢恳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滥邀,臣亦得安愚分。”
乾隆随后将张廷玉的回奏交廷臣集议,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张廷玉不应配享,而且应革去大学士职衔。乾隆说,朕本意并不想停其配享,但张廷玉的举动实在过分,一再乞休不说,还要朕“一言为券”,朕允其请,而其竟谢恩不至。及遇皇长子之丧,甫过初祭即奏回南,于君臣大义及平日师傅恩谊,毫不在意。著照大学士九卿所议,罢其配享,至于所议革去大学士职衔之处,仍著宽免。
习了一辈子臣术,最后还是一败涂地;辛苦了一辈子,最终却丢了伯爵和配享两项荣誉,张廷玉这回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灰溜溜地回老家了。更让他生气的是,其归家之日,地方大员为了避嫌,竟无一人出面迎接。备受打击后,张廷玉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没多久他又惹上了麻烦事。
原来,四川学政朱荃为多捞点主考官的外快而隐瞒母丧消息,其“匿丧赶考”,为御史储磷趾所参。这事本与张廷玉无直接关系,但朱荃曾受张廷玉举荐,两人又是儿女亲家,乾隆厌恶张廷玉,结果把他也给扯上了。事后,乾隆派内务府大臣德保前往张廷玉老家抄查追缴以往三代皇帝对张廷玉的一切赏赐。
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钦差大臣德保来到张家后,随即命人开箱砸柜,大肆查抄,几成挖地三尺之势。所幸的是,张廷玉持身清正,并无太多财产。当然,这并不是德保来此的主要目的,其所奉密旨其实是借追缴名义严查张廷玉的私人文件及藏书,看看老张对乾隆究竟有无怨怼之词。所幸的是,张廷玉为人确实谨慎,德保费了老大劲,仍旧一无所获。
按说,退休高官休致回家后,通常会写点笔记、回忆录什么的,即便不对外公开,给儿孙们看看借以励志也是常有之事。但张廷玉虽留有文字,但绝不涉及政事,更别说什么秘闻了。德保查抄了张廷玉数百封私人书信,但其中均为家常琐事。张廷玉也自编了一本年谱,但其中只记载了自己一生大事,涉及三朝皇帝时只记“恩遇”、“赏赐”,而无一字涉及朝政及机密。完事后,德保对老张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此谨慎,都快成了精了!
既然没抓到张廷玉的把柄,乾隆也只得悻悻然地说,德保实在胡闹,只是让他追缴赏赐之物,如何能胡乱抄张大学士的家?这万一把老人家吓着,看朕不追究你的责任!话虽如此,事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一再打击下,张廷玉自是夹起尾巴,老实做人。据说,其居家期间,日日兀坐家中,终日不发一语。回乡五年后,张廷玉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消息传到京城后,乾隆也觉得自己对张廷玉确实苛刻了点,说“要请之愆,虽由自取,皇考之命,朕何忍违?且张廷玉在皇考时勤慎赞襄,小心书谕,原属旧臣,宜加优恤。应仍谨遵遗诏,配享太庙,以彰我国家酬奖勤劳之盛典。”
如此,被反复折磨多次后,太庙的那块冷猪肉最终还是摆到了张廷玉的嘴边。终清一世,汉大臣而得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而已。略有遗憾的是,张廷玉谥“文和”而未能得“文正”,这或许也说明乾隆仍对其心存芥蒂。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皇帝写诗怀念昔日的五位大学士,其中张廷玉的一首有这样几句,“悬车回故里,乞言定后荣。斯乃不信吾,此念讵宜萌。……后原与配食,遗训敢或更。……斯人而有知,犹应感九京。”
诗后,乾隆自注云:“张廷玉虽有过,余仍不加重谴,仍准以大学士衔休致,及其既卒,仍令配享太庙。余于廷玉曲示保全,使彼泉下有知,当如何衔感乎?”这段话,译成白话就是:张廷玉虽然犯错,但朕并未严惩,仍准许其以大学士衔退休。及至去世,朕仍令其配享太庙。如此优容保全,如张廷玉地下有知,又该当如何感激涕零?
当然,乾隆有时也不乏自知之明。张廷玉去世三十年后,乾隆临雍视学,其想起当年曾欲举行三老五更古礼,“彼时鄂尔泰依违其间,张廷玉则断以为不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自撰三老五更说,命勒碑辟雍,而其所见与张廷玉同。
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复见张廷玉所议,遂命勒碑其次,并题其后,谓张廷玉“有此卓识,乃未见及”,“设尔时勉强行之,必有如廷玉所谓资后人之议者矣”;“盖戊午朕方廿八岁,而戊戌则六十有八,此亦足验四十年间学问识见之效,而年少时犹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至今则洒然矣”;“以识已学之浅深,及弗掩人之善也。夫廷玉既有此卓识,何未见及朕之必不动于浮言。”
最末,乾隆又加了一句,说“朕必遵皇考遗旨,令其配享。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由此可见,乾隆对张廷玉冒犯之事始终未能释怀,这大概也是张廷玉备受折辱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