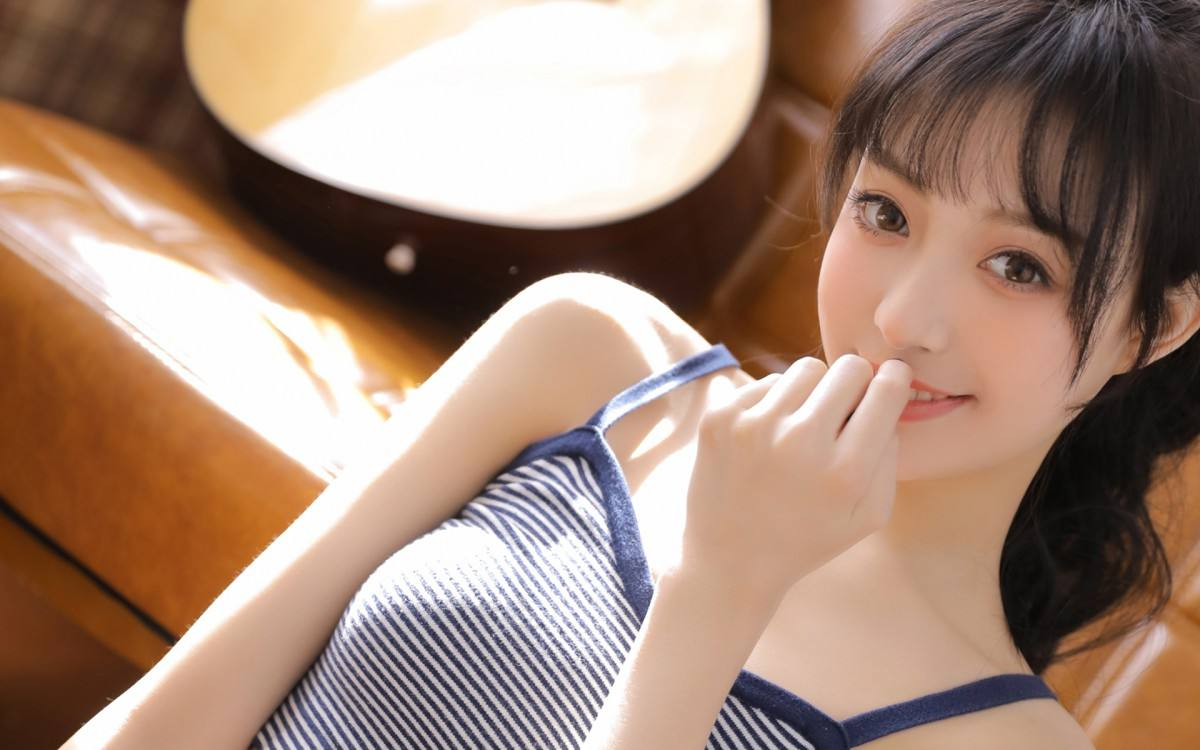江青被囚禁是如何度过的_江青被囚禁地下室的生活概述

1974年,马晓先担任江青的护士长,一直工作到她被隔离审查,从服务到监护。30年来对过去始终缄口不言的马晓先,在2006年2月25日接受《湘潮》杂志采访时,首次曝光了江青被捕后,囚禁于地下室6个月的生活。
李: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的关系密切么?
马:在江青的心里,挺在意张春桥的。她在意的最早的是康生,后来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她要看电影就叫他们两人来,因为王洪文他自己有个屋子专门看电影,他老在家里看。
江青午饭前吃安眠药,吃完就睡觉。晚饭的时候,她就不像中午的时候那样,有时吃完晚饭就要去开会。我经过一次,她吃饭的时候把张春桥给叫来了,又让我到程师傅那儿给他准备一套碗筷。我想真不容易,因为她吃饭的时候不能旁边有人,不能旁边有嚼饭菜的那种声音,只能是放音乐或者是特安静。但那次张春桥就坐在她对面和她一起吃饭。他们是怎么分的菜我就不知道了。他们一直在谈事。
马:后来就是抓江青的事了。我记得抓江青那天是个星期四,当时江青住在中南海的二○一。那天我已经下班了,正在后面洗自己的衣服,穿着双拖鞋。张耀祠就从前面绕过来,平时一般他很少到后边来的。我说,咦,您怎么来了?我感到很吃惊。他说:“小马跟我来一趟!”一看我穿着拖鞋呢,他说:“你把鞋换一下。”我就赶紧把衣服一撂也不洗了,然后回到房间把拖鞋换掉,跟着他后边走。
我也没问他什么事,但是那时候吧我的心里就意识到有事,而且也意识到事情不会小。就跟着走,我也觉得没有必要问他,因为我们多年形成的习惯是不多问。绕过走廊就到大厅的门口,他说:“你开开门咱们进去。”我一到门口呀,一看原来那么大的大厅,两边全站满了武装战士,而且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觉得这事就严重了。
张局长说:“开门进去。”我就把门开了,什么都没说就进去,张局长就跟到我后面进来了。我们进门以后,看到江青在那儿半躺着,她一般办公都是半躺着,一个脚垫踏着。
我就站在那儿,张局长随后就跟她说:“现在我要向你宣布一下中央的决定……从现在开始对你进行隔离审查。”宣布以后江青就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念一遍。”很短的几句话,张耀祠又给她念了一遍。她做了一下调整,就坐在那儿身子也没动,然后就低着头,但是能看得出来脑子在想,在琢磨这事。
张耀祠说:“钥匙该交的你就交一下。”她说:“我交给谁呀?”“你就交给我。”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掏出钥匙来,装进一个牛皮纸的信封,然后拿订书机给订上,很从容的,然后写上“交华国锋同志收”。
她自己就提出来说我要上趟厕所。张耀祠说:“你去吧!”她的厕所就在大厅的边上,她去了。这个时候张局长就跟我说:“给她准备准备东西。”我把她的衣服,换洗的,洗漱用品都给拣了一遍,拣好了给她装进箱子里,那时候因为经常往外跑干这些都熟练了,很快都收拾好了。收拾好后我就从她卧室出来了,出来一看她还在厕所,还没出来,这个时间大概得有10分钟吧。
张耀祠就说:“你进去看看。”然后我就把厕所的门开开进去了。她正蹲在那儿发愣呢!我进去也没说什么,她也知道我的意思是催她。她就稍微想了想,看看我,没说什么话,然后就慢慢悠悠地起来,从卫生间里出来。
这个过程我觉得她显得挺镇静,但是脑子里一直在疑惑,她脑子里一直在想问题,一直在想事情。我把大衣给她披上,她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拎着箱子。打开门,一看有一辆大红旗(我进去时还没有看到有车子),里面坐的都是我们不熟悉的人,都是警卫团的,后来才知道有黄介元、马盼秋、高云江,高云江是押送江青小组的组长。坐在里面以后我记得一边是黄介元,一边是马盼秋,江青坐在中间,我坐在拉开的中间小座上。高云江坐副驾座上。因为那个时候天就已经黑天了,看不太清楚了,黑乎乎地就走了。
李:从这一刻起,您和江青的角色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马:是啊!上了车,车里一个说话的也没有,她也没问什么。车一路开,一直开进地下室,在地下室就转,转了半天。我们下车以后,进了一个房间,一看,我觉得我来过这个地方。周围都是半人多高水曲柳的墙,因为主席的遗体放在那儿的时候江青和姚文元去看过主席的遗体,我陪着去的,所以一进去我就看出来了,我想江青也应该看出来了。一进去,我和江青先在小屋子的床上坐了会儿,江青就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说我也不清楚,她又看看,那儿有个台历,看后她也没吭气。但是,我想她看后心里也已经有数了。
江青最初歇脚的房间成了我们的值班室,有个大厅。她在套间里头,房间大概12到14平米,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有个水池子,有一间卫生间,有个澡盆,应该说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反正从那儿就开始了她的这种生活。
高云江向她宣布了几条规定:在这儿你没有报纸看,可以看书,有《毛选》,你要是想写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纸给你笔。反正给她规定了几条吧!她听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反驳。江青开始几天什么也不做,后来慢慢地,她就开始写点儿东西。
在生活上他们给我交代说:“你现在不能再像以前做护士那样什么都照顾那么周到了,但是别人又不了解她,不好插手,你得在生活上招呼她,但又不能像护士那样亲近,要掌握这个尺度。在生活上,她可以自理的你要教她自己做。” 当时我心里就特别复杂!
李:完全可以想象您当时的感受。不知道江青本人怎么适应这个变化?
马:江青到了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
首先是吃饭,正餐是一荤两素一汤,开始她吃不下去。不想吃工作人员就拿走,后来慢慢地她就吃点了,以后连窝头都要吃半个,一小碗米饭她能吃大半,就比较正常了,跟从前吃的量差不多。偶尔便秘,她还主动多吃点粗粮。我觉得她后来也想通了。
再就是睡觉。睡觉是她一贯的老大难问题,刚开始她可睡不着,折腾,就是把被子一会儿挪到这头来,一会儿挪到那头来,她也不知怎么好——睡不着啊!那都是硬板床,你想这么多年她哪里睡过这种床啊?睡不着就睡不着,睡不着觉了就看看书,拿《毛选》给她看,就是不能给她安眠药。她就整夜地不睡。我说那你在床上休息会儿,睡不着也躺在那儿休息。她也躺着,她也听我的,但她没有睡。因为她的门得敞着不能关,你想我们这都得是公开的,黄介元他们都在这儿坐着,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战士都在那儿站着,她不敢轻易地去说什么话。开始睡不着,后来熬着熬着不知不觉呼呼地也就睡了,人到那种程度也逼出来了。大概3个月以后,她的睡眠逐渐正常了,有规律了。每到晚上,她看我们人少了,比如我也去睡觉了,她也就在那儿和衣呼呼睡了。她从来不脱衣服。因为门不能关,大家都看着,所以她要换衣服就在卫生间小房里换。
江青生活上自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她不会洗衣服,没用过洗衣粉。我说你自己试着洗洗衣服。她说用什么洗啊,我说你就用洗衣粉洗。她拿来洗衣粉就往衣服上倒。我就告诉她,你不能这样,这样就把衣服弄坏了,你得先把衣服放到水池子里,然后把洗衣粉溶化到水里,衣服弄湿后再洗。因为她一开始已经倒了洗衣粉了,就直接把衣服弄湿后洗的,然后搓。她搓不干净,那也只好那样了,反正我告诉她了。后来,她又拿着抹布自己擦擦桌子,再擦擦床,都是慢慢地学,我开始也帮她弄弄,后来就不管了。我看到她写的日记(她写的东西都是公开的,都在那儿摆着),有一条说:“就连小马过去那么温和的、温顺的人,现在也要想骑在我的头上。”其实,我对她真没那么“横”,就是没以前那么体贴周到了。
在这期间,开始几天特别难过,因为我白天要陪她,晚上她不睡觉也得要在那儿陪她。她进到地下室的一个多礼拜,我每天就睡一个多小时。那个时候我觉得压力比较大,精神上也不是太好。就觉得我这护士怎么又变成看守了?这是我的事吗?有时自己想不通,我本来睡觉就不好,又加上连续这么几天心里浮躁,想的东西乱七八糟理不出个头绪来,心里很烦。
于是想找他们要点安眠药,我觉得首先得把觉睡好。我就跟我们送饭的俞师傅说,你给我拿点药吧。他问什么药呀?我说治老毛病的。结果他给我送来了活血化瘀治月经的药。我一看说,你怎么给我送这个药啊?他说那送什么呀?我说治睡不着觉的安眠药。他说那我拿得来呀?他们不会给我的,我要给你送了还不惩治我呀?我也不能让你吃啊!我说不行啊,你要不给我拿来,时间长了我真觉得受不了啊!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有责任我自己担着。又过了一天,他给我带了6片速可眠,哎哟,当时看到速可眠我如获至宝!吃了那个药,睡了一觉缓过来了。
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就跟上面提出再找一个人替换一下,不然我真顶不下来——这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结束。整天也见不着太阳,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再好的东西我也吃不下去,他们看到我那样也不行了,后来就打了个报告。找谁呢?后来从中央办公厅服务处调来一个叫陈世冠的服务员,叫来给我替换一下,我觉得好多了。
李:她来了以后,你和她轮班是一个人12小时吗?
马:不是,平时她不能完全代替我,还是以我为主,她主要是在我睡觉时帮助盯一下。
李:那她盯一下是到套间里呢还是在值班室坐着呢?
马:她就在门口,江青这个门是从来都不关的,白天、晚上或睡觉时都是从来不关的,外面就是一个大厅,我们可以坐在门口也可以坐在大厅,因为套间里面没有椅子。
李:里面有一张床,有一张桌子?
马:对,还有一把椅子,但那椅子都是她坐的,所以我们一般都坐在门口。她的门都不关,她干什么我们都能看得见。她去厕所我都得跟着,以前她去厕所我也得跟着。
有一次,江青要一本杂志类的东西,我们没给她,好像是不允许给。给她看的就是1-4卷《毛选》,其他的不给看。她写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儿规定不许看的,那天正好她写完在那儿摆着,我搞卫生时看到了她写我的那几句,我看她的眼神和对她的态度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我在她那儿工作还算顺利的,她对我也发过脾气,可是对我还算不错,没发生什么大的事情;但该我注意的和做到的我都注意到了、做到了。

李:她这期间跟你谈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吗?不能一句话不说光待着吧?
马:唉呀,这个你觉得不应该是吧?
李:我觉得不应该,您想在这地下半年时间两人面对面什么话都不说,这很难让人想象。
马:实际上挺尴尬的。话呢可能也说,具体的也记不清了。她有时也问,但她问什么,我也都回答不知道。
李:她都问你什么呀?
马:她好像问过外面的谁,但我现在真的记不起来了。
李:是政治方面的、形势方面的吗?比如华国锋、邓小平如何如何?
马:她没问过邓小平他们。
李:她自己写东西的时间多吗?
马:不多。
李:她是一写就是两三个小时,还是简短的两三条呢?
马:就写两三条,想起来了就写,每次大概写个十几分钟吧。
李:她最后交上的东西你没看内容,但您看大概量有多大啊?
马:反正它每张纸也写不满,有时给她收一下,有点什么都给收走了。
李:大概有一寸多厚?
马:嗯,差不多。
李:上面也没什么抬头,如什么中央办公厅之类……
马:对,没什么抬头。铅笔写的。红蓝铅笔,一直是红蓝铅笔。她用惯了铅笔,她也不乱画。
李:在《毛选》上她没有什么批注?
马:没有,没有。《毛选》她就是翻翻看看,你想她什么时候过过这种生活呀?你在那儿监视着我,我在这儿坐着,那个滋味挺难受的。现在看来江青对我们是有戒心的,她对我们有戒心,我们对她也有戒心。
李:比如她也不给你聊点家常什么的?
马:不聊。
李:原来不聊,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会聊些家常啊?
马:原来还聊,这个时候反而不聊了。她会想:我跟小马一说话你墙那边又都知道,再说跟你说也没用啊!
李:这个期间有人来审讯吗?
马:我印象里对她好像组织过一次,这是黄介元他们组织的。我跟你们说黄介元的出面率是最高的。黄介元,年轻,也敢说,比如交代江青干活,就说:“你怎么还不干?这就是你的工作!”她说:“我没干过。”“没干过有人教你啊!”都是这种话,别的也没有什么。
杨:黄介元当时是中央警卫团警卫科副科长。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脸色很严肃;第二个声音大、粗。
马:对,反正说出话来让人害怕,有一定的威力。
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审讯是吧?
马:在地下室没有。
李:有没有领导人下来?
马:没有。那时候就是保证她安全活着,不要出现什么事。
李:除了这几个看押人员外,再也没有什么外人进来?
马:没有,就有一个给她送饭的司机。
杨:送饭的是给你们送还是给她送啊?
马:给我们送也给她送。伙食标准都是一样的,她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对了,我给他们提意见,我说在这儿太难受了,都3个月了不见太阳,就觉得人失去正常的状态了,能不能有什么调节一下?后来他们说:“就你这提议给我们批了个太阳能灯下来。”大家轮流坐在那儿照一照。我一直待在那儿3个月,后来中间让我回去了一趟。

李:她每天的作息时间怎么安排?
马:开始我觉得挺乱的,但所谓的乱就是她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折腾,她也不知怎么好。她也分不清白天黑夜,因为她没有表,有时问问我几点了。后来她睡眠逐渐好了,基本上有规律了,可能是在3个月以后,每天到了晚上她就去睡了。
李:她一般睡觉都在10点来钟?
马:10点钟她不会睡的,睡不着。大概十一二点睡吧,睡眠还可以,比我都好,有时还有点小呼噜。
李:从常人的角度考虑,人到这种时候比较孤独,这么大的命运转折的时候,会希望有人可以倾诉,特别是女性,是不是更需要一种排遣甚至宣泄?
马:她不,她跟一般人不一样,没听过她主动给人说什么。
李:你说她十一二点睡,那她早上几点起啊?
马:早上大概六七点钟,有时五六点钟醒来,但这个时候少,一般都是六七点钟起来,起来以后自己刷刷牙,洗洗脸,梳梳头,反正这些事情都是她自己弄,毛巾也是她自己洗,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很正常了。
李:7点30分早餐,这应该是很规律的吧?
马:对。然后,上午有时她自己在屋子里散散步,不出她的屋子,就从她的大屋子到卫生间,从卫生间到大屋子,来回这么走走,有时是背着手,像若有所思的样子,有时坐在椅子上翻翻书,有时就写写,一天基本上是这样。中午吃完饭她也睡会儿觉。大概躺一个小时,不一定能睡着,我们不叫她,她想睡到什么时候就睡到什么时候。
李:她上午和下午基本做的事都差不多,实际上是没事?
马:确实没事。她所谓的事就是吃饭、睡觉、散散步,然后看看东西,写点东西。
李:她躺着的时候多还是坐着的时候多?
马:差不多,两个比较起来还是躺着的时候多。坐的时候她坐在凳子上,桌子上有一摞书,还有纸、笔,就像在家里,但不像在家里办公,在这儿她就拿着一本书翻着。看书她都坐在凳子上,很少躺在床上看书,要躺就躺在床上一会儿。她这段时间还是相对自由的,想看书就看书,想写东西就写东西,想散步就散步,想上厕所就上厕所,她只要不违规,我们一般不去管她。 开始她还是有些便秘,在马桶上时间挺长的。
李:她饭量怎么样?
马:开始她吃不下,有的东西拿过来最后又拿走了,不过我觉得这段时间不长,也就几天的时间,后来慢慢就吃了,跟过去吃的差不多,饭量还可以。一小碗米饭她能吃大半,后来我觉得她吃的还真不少。她自己也知道,她说大便还是有点干,还是多吃点粗粮。
别的我不管,我就是执行上面的政策,保证任务完成,保证她的安全。我的身份是护士,从医疗保健的角度出发,过去是保证她怎样健康,现在我就是要保证她安全,不出什么事。她有怨言只能给我发,我说我也不愿意在这儿待,弄得我比过去还累,本来交班以后可以睡个大觉,可是我现在只能坚持着、熬着。在表面上我又不能表现出疲劳、憔悴,所以我要求要照照光线什么的,以使自己精神点儿。
李:她有没有大吵大闹的时候?
马:没有。情绪上肯定有大的波动,但她没有表现出来,没有像有些人似的胡搅蛮缠。天天看她还是利利索索的,一点儿都不邋遢。
李:她的衣服这时候是不是都变成黑的了?
马:大部分是,也有蓝的。主席一去世她把所有的衣服,毛衣什么的都染成黑色的了。我在那儿的时候她都是穿自己的衣服。
去秦城监狱之前,我接到命令给她收拾东西的时候,她出来时穿什么衣服还给她带什么衣服,给她打理好,然后放在车上,我和她一块坐在车里走的。那天早上太阳特别好,光线也特别好,一直走了很远,走到秦城,就到监狱了……
李:请你把这个过程说细一点儿。
马:1977年4月10日,交接押送任务下来后,黄介元给我打了招呼。他说凌晨要转移地方了,先让我自己作好准备,把她身边的东西都拾掇好。我们一切都听黄介元的指挥,他问我:“你们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我说都准备好了。然后他就走到江青的门口(他一般就站在门口不进她的屋子),对江青说:“今天要换个地方,戴上这个吧!”江青说:“好吧!”缓慢走进卫生间,出来后,顺从地戴上手铐。我带着江青的衣物和她坐在一辆车里,她一路上没说一句话。
李:江青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马:没有。有时候外边传的跟实际情况有天地之别。她当时确实是很平静,她对于自己的道路好像早就料到了。到秦城监狱后,两名女狱警把她架进了牢房。
李:架进去的?
马:反正一边一个把她带进去了。监狱的人把江青带进去,我们向狱警介绍了江青的饮食和睡眠等,交接了衣物。送她的人就随着车回来了。
杨:路途中间听说她还要求解手?
马:她是说要解手,但押解的人告诉她很快就到了。
李:送到以后她就离开你的视线了?
马:对。
李:你当时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她了?
马:意识到了。但是我想国家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毕竟是主席的夫人。但是她不会有太多的自由,这个是肯定的。
从1976年10月6日到1977年4月10日,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四人帮”的任务胜利完成,总共187天。这6个多月,我都过糊涂了,一直以为是3个月,中间我只回过一次家。这一天是我几个月以来又可以呼吸清新空气、重新沐浴温暖阳光的难忘的一天。
马:时隔这么多年,回想起来,在工作人员当中,我还算是遭罪少的。她平时好像没怎么说我什么。因为我是她要来的,几个条件都符合,又是科班出身的,又是有个孩子的,她又认为我的性格比较温柔,所以对我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
总的来说,她的衣食住行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除了脾气不好外。而且我们觉得她在吃的方面还有一定的科学性,一般也没有什么高档东西;穿衣上不讲究什么时髦,只讲究如何保暖,衣服她不愿意穿太新的,里边的衬衣都是旧的,棉质的;擦脸霜是小药房配制的,她从来也不用化妆品。也没有戴过任何首饰;行呢,也就是坐车坐的时间长了,会让汽车停下来,我们扶着她散散步什么的。
我们做她的护士肯定是闲不住的,在家里闲不住,出去闲不住,车上也闲不住,但是你要想想她要求的服务内容和方式都是对保健很有益的、适时的。比如快到冬天了,秋末就把冬天的衣服给找出来了。冬天过了快到春天的时候,春天的衣服就都给准备出来了。我所说的这一套衣服不是一件两件,从衬衣到外衣、大衣都是搭配的,颜色都是顺色搭配的,我就觉得她这些都很讲究但又是合乎生理需要的,穿上以后又特别得体。
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她的心灵手巧也是让人佩服的,你看她穿的衣服有一套蓝裙子,那是她自己设计的。1974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来访,为了体现主席夫人的形象和中国自己民族服装的特色,她专门按照唐三彩的样子设计了一些衣服,圆领的服装,里面带个白边,她说这个代表民族的特色,她说:“我先来试穿。”这样她就把她的好多衬衫都改成没领的衬衫,还建议女战士的衬衣、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衣服也都改成这样的。她做这套衣服的时候,问我们这样好不好,我觉得这样也挺新颖的,说那就试试。
后来浩亮、于会泳他们几个还按她的要求给弄了两套假发,她当时是想弄两个辫子给盘上去,我的理解她主要是想显得高雅一点。这个我们说看着不习惯呀,她后来就没穿出去。这意见她是听进去了。我觉得在这件事上,实际上她不是光为她个人美,也是考虑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江青一边在马桶上蹲着一边还看文件,有的还送主席参阅。当然,我觉得她对自己是高估了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她把邓小平叫到十楼来,当面指着邓小平的鼻子说:“嗯,主席对你三七开,对我四六开我就满足了。”意思是主席对你够好的了。
不管怎么说,我对在包括江青在内的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这些经历都不感到后悔。